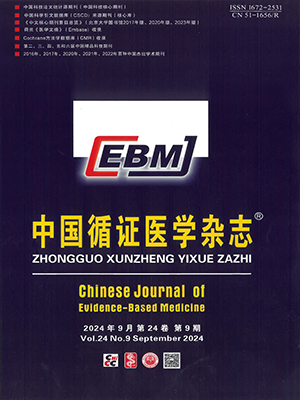引用本文: 周涛, 刘权辉, 杨紫陌, 廖敬仪, 杨可心, 白薇, 吕欣, 张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基本再生数的初步预测.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0, 20(3): 359-364. doi: 10.7507/1672-2531.202001118 复制
截至 2020 年 1 月 26 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 2019-nCoV)的全国各地确诊和疑似病例数仍在快速上升,疾病传播发展趋势尚无研究进行评估。如何采用合适的模型和数据,评估 2019-nCoV 流行病动力学的关键参数高低,对于评价疾病传播能力、预测传播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并能够为制定相应的干预和防控措施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
基本再生数(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R0)是指在一个全是易感染态个体构成的群体中,一个感染态的个体在恢复之前平均能感染的人数。在流行病学中,R0>1 表示疾病将爆发,<1 则表示疾病走向消亡,故 R0 是判断流行病是否爆发的重要条件之一[1]。但在真实疫情的传播过程中,由于政府干预政策实施、个体行为改变(戴口罩、减少出行等)、易感人群数量减少(因患病人数增多或使用疫苗等)等外在因素影响,不再满足基本再生数定义的理想模型条件。为刻画流行病随时间的演化过程,我们将传播过程中某一时刻下(t)平均一个感染态个体感染的人数定义为有效再生数,记为 Rt。在实际疫情的控制过程中,当 Rt<1 时,即平均一个感染态个体感染的人数小于 1 时,认为疾病已被控制同时疾病也将走向消亡。
本文假设 2020 年 1 月 25 日及以前出现症状的感染者均是在 2019-nCoV 无干预自由传播期间感染,参考《人民日报》[2]和丁香园[3]共同发布的 2019-nCoV 疫情实时动态数据和国际同行特别是美国东北大学对 2019-nCoV 感染人数的估计结果[4],基于包括“易感态-潜伏态-感染态-移除态”的 SEIR 仓室模型计算 2019-nCoV 的基本再生数。
1 资料与方法
1.1 无干预自由传播期的设定
2020 年 1 月 21 日,中国主流媒体开始对 2019-nCoV 的地区间传播进行报道。2020 年 1 月 22 日凌晨 2:40,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通告》,同时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在此之前,普通群众缺乏对 2019-nCoV 的认知渠道和宣传力度,一般民众尚未做出相关的行为改变(如戴口罩、勤洗手等)来响应疫情防控,2019-nCoV 的传播处于无干预自由传播期。
与 2019-nCoV 类似的 SARS 病毒潜伏期中位数为 6.4 天(95%CI 为 5.2~7.7 天)[5],同时根据 Chan 等[6]对 9 位 2019-nCoV 早期确诊病例已知潜伏期的分析结果显示其平均潜伏期为 5.1 天。因此可近似认为 2020 年 1 月 25 日及以前确诊的病例几乎都是在没有有效干预和防控手段的情况下自由感染所致。而 1 月 25 日(武汉封城)后确诊的病例则不再符合无干预自由传播的定义。
1.2 建立 SEIR 模型
将 2019-nCoV 早期的自由传播用一个包括“易感态-潜伏态-感染态-移除态”的 SEIR 仓室模型来描述[7]。其中 S 代表易感人群,E 代表被感染后处于潜伏期的人群,I 代表潜伏期之后已具有感染能力的人群,R 表示已经因为治愈并获得免疫、被有效隔离、因病死亡等原因已经不对流行病传播动力学产生影响的人群。
假设一个感染态个体(I 态)与易感染态个体(S 态)接触,易感染态个体被感染进入潜伏期的概率(传染率)为 β;一个处于潜伏期的 E 态个体单位时间内将以概率 γ1 转变为 I 态;一个 I 态个体单位时间内将以概率 γ2 转变为 R 态(单位时间为天)。
显然,SEIR 传播过程可用下述 4 个微分方程进行描述:
 |
其中,S(t)、E(t)、I(t) 和 R(t) 分别表示 t 时刻网络中处于易感态、潜伏态、感染态和移除态的个体数目。N 表示系统中个体总数目,且 N=S(t)+E(t)+I(t)+R(t)。
1.3 基本再生数公式
早期自由传播期感染的人数与总人口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当 t 趋近于 0 时,S(t) 趋近于 N,此时基本再生数 R0 可表示为:
 |
其中  是早期指数增长时的增长率,Y(t)是截至到 t 时刻有症状的感染人数。潜伏期和感染期可分别表示为
是早期指数增长时的增长率,Y(t)是截至到 t 时刻有症状的感染人数。潜伏期和感染期可分别表示为  和
和  ,生成时间(generation time)可近似为序列间隔,即
,生成时间(generation time)可近似为序列间隔,即  。记
。记  为潜伏期占生成时间的比例,则基本再生数可表示为:
为潜伏期占生成时间的比例,则基本再生数可表示为:
 |
2 结果
2.1 基本再生数的关键参数
要估计 R0,关键参数是 λ、ρ 和Tg,而 λ 可由 Y(t) 确定。故我们用《人民日报》数据和国外同行的预测结果来确定 3 个关键参数的上下限。
2.1.1 Y(t) 的上下限
截至 2020 年 1 月 25 日 23:59,《人民日报》报告的 2019-nCoV 疫情实时动态数据为:确诊 1 408 例,疑似 2 032 例。根据当前防控实际情况,存在一定比例的有症状的感染态个体还未被发现[4, 9, 10]。如果暂不考虑此情况,并假设疑似病例中有 q 的概率处于感染态。初期报导提到 59 个疑似病例有 41 位最终确诊,因此 q 的参考值为 41/59=0.695。当 q=0.695 时,则 1 月 25 日被感染人数为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考虑到因检测盒缺乏等不同因素导致各地疫情上报的滞后性,实际已出现症状的感染人数应当超过 2 820 例。故我们将此数值作为 Y(t) 下限值。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考虑到因检测盒缺乏等不同因素导致各地疫情上报的滞后性,实际已出现症状的感染人数应当超过 2 820 例。故我们将此数值作为 Y(t) 下限值。
若以美国东北大学 Chinazzi 等[4]的预测结果为参考,则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约有 4 050 例感染者,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约有 12 700 例感染者。该研究主要以武汉出境后在境外被确诊的病患数目进行估计,因样本量较少,分析逻辑简单,结果出现的误差可能较大,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国际上其他预测结果[7, 8]与 Chinazzi 等[4]接近。Read 等[8]推测 2019-nCoV 实际确诊人数占比仅 5.1%(这里面也包含还没有出现症状的感染者)。而当我们假设最悲观情况,即只有 5% 的有症状感染者被检测出来,则根据截至到 1 月 25 日的确诊人数 1 408 例,2019-nCoV 的有症状感染者约为 28 160 例,恰为乐观情况的 10 倍。虽然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很可能估计过高,因此不作为主要参考,但是在做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时候,将其作为 Y(t) 的上限。
我们将第 1 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报道时间 2019 年 12 月 8 日设为t=0,实际上这个时间可能略早于 12 月 8 日,因为可能症状已出现了一段时间才会就医。将 2019 年 12 月 8 日作为时间起点(t=0),估计得到的基本再生数可能会略高。以《人民日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数据为基准,则得出 Y(48)=2 820 例;以美国东北大学报告为基准,则有 Y(43)=4 050 例和 Y(47)=12 700 例。
2.1.2 ρ 值
已有研究结果显示,SARS 传播的 ρ 取值在 0.5~0.8 之间[5, 11]。在没有更多可参考数据的情况下,我们设定 2019-nCoV 的 ρ=0.65。在做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时候,我们考虑了 ρ 从 0.5 到 1 的情。因为  具有对称性,这实际覆盖了所有可能的 ρ 的取值。
具有对称性,这实际覆盖了所有可能的 ρ 的取值。
2.1.3 Tg值
Lipsitch 等[12]对 SARS 传播数据的分析显示,均值在 8.4 天。Lipsitch 等认为疾病爆发早期 Tg 或许更高(均值为 10.0),建议敏感性分析的 Tg 区间为 。Imai 等[13]认为 Chan 等[6]的结果预示 2019-nCoV 有更短的 Tg。但我们认为,Chan 等的结果数据量太小且 Imai 等的推断尚不可靠的缘由(Tg越小基本再生数越小,传播能力越弱),故我们基于 Tg=8.4 和 Tg=10.0 两个取值进行分析,在做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时候,采用与 Lipsitch 等[12]相同的 Tg 区间(10, 14)。
。Imai 等[13]认为 Chan 等[6]的结果预示 2019-nCoV 有更短的 Tg。但我们认为,Chan 等的结果数据量太小且 Imai 等的推断尚不可靠的缘由(Tg越小基本再生数越小,传播能力越弱),故我们基于 Tg=8.4 和 Tg=10.0 两个取值进行分析,在做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时候,采用与 Lipsitch 等[12]相同的 Tg 区间(10, 14)。
2.2 基本再生数计算结果
基于 SEIR 模型估计得到的 R0 和对应的关键参数取值见表 1。
从表 1 中可以得出,如果以《人民日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数据为基准,R0 约在 2.8~3.3 之间;如果以美国东北大学的报告为基准,R0 约在 3.2~3.9 之间。
美国东北大学和 Read 等[10]对 R0 估计为 3.6~4.0。而本研究结果要高于近期 Imai 等[13]估计的结果[中位数 2.6(2.1,3.5)]。
2.3 关键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结果
R0 的 3 个主要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见图 1。在最坏的参数条件下( ,
, ,
, ),基本再生数估计值为 5.2;在最好的参数条件下(
),基本再生数估计值为 5.2;在最好的参数条件下( ,
, ,
, ),R0 估计值为 2.3。因基本再生数的取值对于生成时间非常敏感,后期随着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的丰富,如能更精确估计生成时间,将得到更准确的 R0 值。
),R0 估计值为 2.3。因基本再生数的取值对于生成时间非常敏感,后期随着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的丰富,如能更精确估计生成时间,将得到更准确的 R0 值。
 图1
基本再生数 3 个关键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图1
基本再生数 3 个关键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横坐标是
3 讨论
3.1 2019-nCoV 属于属于传染能力中等略偏高的传染病
根据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2019-nCoV 基本再生数在(2.3,5.2)之间,但因上限结果为极限设定,如果以《人民日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数据为基准,R0 应在(2.8,3.3)之间;如果以美国东北大学的报告为基准,R0 应在(3.2,3.9)之间,故我们认为 R0 应在(2.8,3.9)之间。如果我们以《人民日报》和丁香园联合发布的实时数据进行计算,2019-nCoV 的 R0 不高于 SARS,甚至略低于一些研究团队报告的 SARS 的 R0。Lipsitch 等[12]给出的 SARS 的 R0=(2.2,3.6),Riely 等[14]给出 SARS 的 R0=2.7(2.2,3.7),但若考虑超级传播者,则这个均值可上升到 3.4。Wallinga 等[15]给出 SARS 的 R0=(3.1,4.2)。以上数据显示,即便采用国际上相关研究团队较为悲观的预测感染人数,2019-nCoV 的 R0 也只是略高于 SARS,属于传染能力中等略偏高的传染病。很多已知传染病的 R0 估计区间都整体高于 2019-nCoV,例如寨卡病毒的 R0=(1.4,6.6)[16],中东呼吸综合症的 R0=(2.0,6.7)[17],天花的 R0=(2.5,6.0)[18]。故 2019-nCoV 并不具体特别突出的传染能力,属于传染能力中等略偏高的传染病。根据我们对抗 SARS 的经验,在这种疾病传播能力下,政府通过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可以较快抑制传染病的进一步蔓延。
3.2 R0 的结果准确性
根据参数敏感性分析可知,本方法得到的结果对于生成时间 Tg 最敏感。后期随着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的丰富,能够更精确估计生成时间,就可得到更准确 R0。目前,从不同来源得到的确诊患者数目相差很大,甚至可差一个数量级,而后期随着确诊病人回访数据的采集,应该能够对自由传播期间的感染人数有更准确的判断。由于 2019-nCoV 有相当比例的病人症状很轻且可以自愈,因为肯定会有部分患者不在官方确诊和上报的数据中,所以我们建议谨慎采信基于东北大学报告的结果。虽然我们的模型假设潜伏期没有传染能力或传染性非常低,但有可能 2019-nCoV 在潜伏期是具有相当传染性。因其影响我们在分析全区间 ρ 的取值时已经考虑在内了,不会对结果造成很大偏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研究是在数据比较缺乏前提下的一个初步估计。如何准确估计 2019-nCoV 的基本再生数和有效再生数并预测传播趋势模型,不仅需要在本模型下更准确知道相关关键参数,更要对模型本身进行修正,使之更符合实际,如包括考虑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群易感性的不同和接触概率的不同、分开考虑医院内的传播和医院外的传播、考虑区域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性对于传播的影响等[19-22]。
3.3 阻断 2019-nCoV 传播的关键参数
从疾病传播动力学的观点来看,有效再生率R0=kβD,其中 k 是一个有传染能力的感染者平均每天与易感人群的可能导致传染的接触数量,β 是每次接触的传染率,D 是可传播的时间长度。目前我国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社会媒体对普通群众强化宣传如何减少疾病传播和一般人群采用自我保护措施均能有效降低 k、β、D 值,最终使有效再生数 Rt 下降到 1 以下。根据我们的结果,如果 k、β、D 值能够降到原来的 1/4,2019-nCoV 就能得到有效控制。
少出门和不聚会可降低感染者和易感者接触的机会(k),戴口罩和勤洗手可降低传染率(β),如果出现疑似症状或者与高危人群有密切接触后,自己在家隔离或接受医学观察,可缩短传播时间(D)。目前政府采用交通管制、延长企业开工和学校开学时间、取消会议和公众聚会也能够有效、尽快地降低有效再生数。
从目前已经获知信息来看,相当一部分 2019-nCoV 的感染者仅表现为轻微症状,他们原则上具有和健康人一样的活动能力。有一些初期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提示 2019-nCoV 在潜伏期具备一定传染性。再加上武汉出台防控政策时已错过黄金时间,导致 2019-nCoV 的初期传播势头显得比 SARS 还要凶猛。但我们认为,只要按照国家部署和各级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对 2019-nCoV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对疑似患者(包括潜伏期和轻微症)患者进行隔离和治疗,采用“小汤山医院”模式对重症患者进行强化治疗,严防医院感染,做好自我保护,全面减少和其他人的接触,根据我们抗击 SARS 的经验,2019-nCoV 将会很快得到有效控制。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收集 2019-nCoV 在自由传播状态下的病例数据,采用 SEIR 模型预测得到 2019-nCoV 传播初期的基本再生数略高于 SARS 病毒,表明 2019-nCoV 属于中高度传染性的传播疾病。为尽快控制 2019-nCoV 蔓延,需要在切断传染源、降低传染率和缩短传播时间的各环节进行有效防控。此外,本文在预测的过程中,采用了与 SARS 传播初期的相关参数,且发现预测得到的基本再生数对生成时间敏感。未来为了得到更准确的预测结果,还需更多微观传播的数据对模型和参数进行调整。
截至 2020 年 1 月 26 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 2019-nCoV)的全国各地确诊和疑似病例数仍在快速上升,疾病传播发展趋势尚无研究进行评估。如何采用合适的模型和数据,评估 2019-nCoV 流行病动力学的关键参数高低,对于评价疾病传播能力、预测传播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并能够为制定相应的干预和防控措施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
基本再生数(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R0)是指在一个全是易感染态个体构成的群体中,一个感染态的个体在恢复之前平均能感染的人数。在流行病学中,R0>1 表示疾病将爆发,<1 则表示疾病走向消亡,故 R0 是判断流行病是否爆发的重要条件之一[1]。但在真实疫情的传播过程中,由于政府干预政策实施、个体行为改变(戴口罩、减少出行等)、易感人群数量减少(因患病人数增多或使用疫苗等)等外在因素影响,不再满足基本再生数定义的理想模型条件。为刻画流行病随时间的演化过程,我们将传播过程中某一时刻下(t)平均一个感染态个体感染的人数定义为有效再生数,记为 Rt。在实际疫情的控制过程中,当 Rt<1 时,即平均一个感染态个体感染的人数小于 1 时,认为疾病已被控制同时疾病也将走向消亡。
本文假设 2020 年 1 月 25 日及以前出现症状的感染者均是在 2019-nCoV 无干预自由传播期间感染,参考《人民日报》[2]和丁香园[3]共同发布的 2019-nCoV 疫情实时动态数据和国际同行特别是美国东北大学对 2019-nCoV 感染人数的估计结果[4],基于包括“易感态-潜伏态-感染态-移除态”的 SEIR 仓室模型计算 2019-nCoV 的基本再生数。
1 资料与方法
1.1 无干预自由传播期的设定
2020 年 1 月 21 日,中国主流媒体开始对 2019-nCoV 的地区间传播进行报道。2020 年 1 月 22 日凌晨 2:40,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通告》,同时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在此之前,普通群众缺乏对 2019-nCoV 的认知渠道和宣传力度,一般民众尚未做出相关的行为改变(如戴口罩、勤洗手等)来响应疫情防控,2019-nCoV 的传播处于无干预自由传播期。
与 2019-nCoV 类似的 SARS 病毒潜伏期中位数为 6.4 天(95%CI 为 5.2~7.7 天)[5],同时根据 Chan 等[6]对 9 位 2019-nCoV 早期确诊病例已知潜伏期的分析结果显示其平均潜伏期为 5.1 天。因此可近似认为 2020 年 1 月 25 日及以前确诊的病例几乎都是在没有有效干预和防控手段的情况下自由感染所致。而 1 月 25 日(武汉封城)后确诊的病例则不再符合无干预自由传播的定义。
1.2 建立 SEIR 模型
将 2019-nCoV 早期的自由传播用一个包括“易感态-潜伏态-感染态-移除态”的 SEIR 仓室模型来描述[7]。其中 S 代表易感人群,E 代表被感染后处于潜伏期的人群,I 代表潜伏期之后已具有感染能力的人群,R 表示已经因为治愈并获得免疫、被有效隔离、因病死亡等原因已经不对流行病传播动力学产生影响的人群。
假设一个感染态个体(I 态)与易感染态个体(S 态)接触,易感染态个体被感染进入潜伏期的概率(传染率)为 β;一个处于潜伏期的 E 态个体单位时间内将以概率 γ1 转变为 I 态;一个 I 态个体单位时间内将以概率 γ2 转变为 R 态(单位时间为天)。
显然,SEIR 传播过程可用下述 4 个微分方程进行描述:
 |
其中,S(t)、E(t)、I(t) 和 R(t) 分别表示 t 时刻网络中处于易感态、潜伏态、感染态和移除态的个体数目。N 表示系统中个体总数目,且 N=S(t)+E(t)+I(t)+R(t)。
1.3 基本再生数公式
早期自由传播期感染的人数与总人口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当 t 趋近于 0 时,S(t) 趋近于 N,此时基本再生数 R0 可表示为:
 |
其中  是早期指数增长时的增长率,Y(t)是截至到 t 时刻有症状的感染人数。潜伏期和感染期可分别表示为
是早期指数增长时的增长率,Y(t)是截至到 t 时刻有症状的感染人数。潜伏期和感染期可分别表示为  和
和  ,生成时间(generation time)可近似为序列间隔,即
,生成时间(generation time)可近似为序列间隔,即  。记
。记  为潜伏期占生成时间的比例,则基本再生数可表示为:
为潜伏期占生成时间的比例,则基本再生数可表示为:
 |
2 结果
2.1 基本再生数的关键参数
要估计 R0,关键参数是 λ、ρ 和Tg,而 λ 可由 Y(t) 确定。故我们用《人民日报》数据和国外同行的预测结果来确定 3 个关键参数的上下限。
2.1.1 Y(t) 的上下限
截至 2020 年 1 月 25 日 23:59,《人民日报》报告的 2019-nCoV 疫情实时动态数据为:确诊 1 408 例,疑似 2 032 例。根据当前防控实际情况,存在一定比例的有症状的感染态个体还未被发现[4, 9, 10]。如果暂不考虑此情况,并假设疑似病例中有 q 的概率处于感染态。初期报导提到 59 个疑似病例有 41 位最终确诊,因此 q 的参考值为 41/59=0.695。当 q=0.695 时,则 1 月 25 日被感染人数为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考虑到因检测盒缺乏等不同因素导致各地疫情上报的滞后性,实际已出现症状的感染人数应当超过 2 820 例。故我们将此数值作为 Y(t) 下限值。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考虑到因检测盒缺乏等不同因素导致各地疫情上报的滞后性,实际已出现症状的感染人数应当超过 2 820 例。故我们将此数值作为 Y(t) 下限值。
若以美国东北大学 Chinazzi 等[4]的预测结果为参考,则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约有 4 050 例感染者,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约有 12 700 例感染者。该研究主要以武汉出境后在境外被确诊的病患数目进行估计,因样本量较少,分析逻辑简单,结果出现的误差可能较大,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国际上其他预测结果[7, 8]与 Chinazzi 等[4]接近。Read 等[8]推测 2019-nCoV 实际确诊人数占比仅 5.1%(这里面也包含还没有出现症状的感染者)。而当我们假设最悲观情况,即只有 5% 的有症状感染者被检测出来,则根据截至到 1 月 25 日的确诊人数 1 408 例,2019-nCoV 的有症状感染者约为 28 160 例,恰为乐观情况的 10 倍。虽然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很可能估计过高,因此不作为主要参考,但是在做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时候,将其作为 Y(t) 的上限。
我们将第 1 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报道时间 2019 年 12 月 8 日设为t=0,实际上这个时间可能略早于 12 月 8 日,因为可能症状已出现了一段时间才会就医。将 2019 年 12 月 8 日作为时间起点(t=0),估计得到的基本再生数可能会略高。以《人民日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数据为基准,则得出 Y(48)=2 820 例;以美国东北大学报告为基准,则有 Y(43)=4 050 例和 Y(47)=12 700 例。
2.1.2 ρ 值
已有研究结果显示,SARS 传播的 ρ 取值在 0.5~0.8 之间[5, 11]。在没有更多可参考数据的情况下,我们设定 2019-nCoV 的 ρ=0.65。在做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时候,我们考虑了 ρ 从 0.5 到 1 的情。因为  具有对称性,这实际覆盖了所有可能的 ρ 的取值。
具有对称性,这实际覆盖了所有可能的 ρ 的取值。
2.1.3 Tg值
Lipsitch 等[12]对 SARS 传播数据的分析显示,均值在 8.4 天。Lipsitch 等认为疾病爆发早期 Tg 或许更高(均值为 10.0),建议敏感性分析的 Tg 区间为 。Imai 等[13]认为 Chan 等[6]的结果预示 2019-nCoV 有更短的 Tg。但我们认为,Chan 等的结果数据量太小且 Imai 等的推断尚不可靠的缘由(Tg越小基本再生数越小,传播能力越弱),故我们基于 Tg=8.4 和 Tg=10.0 两个取值进行分析,在做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时候,采用与 Lipsitch 等[12]相同的 Tg 区间(10, 14)。
。Imai 等[13]认为 Chan 等[6]的结果预示 2019-nCoV 有更短的 Tg。但我们认为,Chan 等的结果数据量太小且 Imai 等的推断尚不可靠的缘由(Tg越小基本再生数越小,传播能力越弱),故我们基于 Tg=8.4 和 Tg=10.0 两个取值进行分析,在做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时候,采用与 Lipsitch 等[12]相同的 Tg 区间(10, 14)。
2.2 基本再生数计算结果
基于 SEIR 模型估计得到的 R0 和对应的关键参数取值见表 1。
从表 1 中可以得出,如果以《人民日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数据为基准,R0 约在 2.8~3.3 之间;如果以美国东北大学的报告为基准,R0 约在 3.2~3.9 之间。
美国东北大学和 Read 等[10]对 R0 估计为 3.6~4.0。而本研究结果要高于近期 Imai 等[13]估计的结果[中位数 2.6(2.1,3.5)]。
2.3 关键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结果
R0 的 3 个主要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见图 1。在最坏的参数条件下( ,
, ,
, ),基本再生数估计值为 5.2;在最好的参数条件下(
),基本再生数估计值为 5.2;在最好的参数条件下( ,
, ,
, ),R0 估计值为 2.3。因基本再生数的取值对于生成时间非常敏感,后期随着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的丰富,如能更精确估计生成时间,将得到更准确的 R0 值。
),R0 估计值为 2.3。因基本再生数的取值对于生成时间非常敏感,后期随着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的丰富,如能更精确估计生成时间,将得到更准确的 R0 值。
 图1
基本再生数 3 个关键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图1
基本再生数 3 个关键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横坐标是
3 讨论
3.1 2019-nCoV 属于属于传染能力中等略偏高的传染病
根据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2019-nCoV 基本再生数在(2.3,5.2)之间,但因上限结果为极限设定,如果以《人民日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数据为基准,R0 应在(2.8,3.3)之间;如果以美国东北大学的报告为基准,R0 应在(3.2,3.9)之间,故我们认为 R0 应在(2.8,3.9)之间。如果我们以《人民日报》和丁香园联合发布的实时数据进行计算,2019-nCoV 的 R0 不高于 SARS,甚至略低于一些研究团队报告的 SARS 的 R0。Lipsitch 等[12]给出的 SARS 的 R0=(2.2,3.6),Riely 等[14]给出 SARS 的 R0=2.7(2.2,3.7),但若考虑超级传播者,则这个均值可上升到 3.4。Wallinga 等[15]给出 SARS 的 R0=(3.1,4.2)。以上数据显示,即便采用国际上相关研究团队较为悲观的预测感染人数,2019-nCoV 的 R0 也只是略高于 SARS,属于传染能力中等略偏高的传染病。很多已知传染病的 R0 估计区间都整体高于 2019-nCoV,例如寨卡病毒的 R0=(1.4,6.6)[16],中东呼吸综合症的 R0=(2.0,6.7)[17],天花的 R0=(2.5,6.0)[18]。故 2019-nCoV 并不具体特别突出的传染能力,属于传染能力中等略偏高的传染病。根据我们对抗 SARS 的经验,在这种疾病传播能力下,政府通过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可以较快抑制传染病的进一步蔓延。
3.2 R0 的结果准确性
根据参数敏感性分析可知,本方法得到的结果对于生成时间 Tg 最敏感。后期随着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的丰富,能够更精确估计生成时间,就可得到更准确 R0。目前,从不同来源得到的确诊患者数目相差很大,甚至可差一个数量级,而后期随着确诊病人回访数据的采集,应该能够对自由传播期间的感染人数有更准确的判断。由于 2019-nCoV 有相当比例的病人症状很轻且可以自愈,因为肯定会有部分患者不在官方确诊和上报的数据中,所以我们建议谨慎采信基于东北大学报告的结果。虽然我们的模型假设潜伏期没有传染能力或传染性非常低,但有可能 2019-nCoV 在潜伏期是具有相当传染性。因其影响我们在分析全区间 ρ 的取值时已经考虑在内了,不会对结果造成很大偏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研究是在数据比较缺乏前提下的一个初步估计。如何准确估计 2019-nCoV 的基本再生数和有效再生数并预测传播趋势模型,不仅需要在本模型下更准确知道相关关键参数,更要对模型本身进行修正,使之更符合实际,如包括考虑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群易感性的不同和接触概率的不同、分开考虑医院内的传播和医院外的传播、考虑区域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性对于传播的影响等[19-22]。
3.3 阻断 2019-nCoV 传播的关键参数
从疾病传播动力学的观点来看,有效再生率R0=kβD,其中 k 是一个有传染能力的感染者平均每天与易感人群的可能导致传染的接触数量,β 是每次接触的传染率,D 是可传播的时间长度。目前我国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社会媒体对普通群众强化宣传如何减少疾病传播和一般人群采用自我保护措施均能有效降低 k、β、D 值,最终使有效再生数 Rt 下降到 1 以下。根据我们的结果,如果 k、β、D 值能够降到原来的 1/4,2019-nCoV 就能得到有效控制。
少出门和不聚会可降低感染者和易感者接触的机会(k),戴口罩和勤洗手可降低传染率(β),如果出现疑似症状或者与高危人群有密切接触后,自己在家隔离或接受医学观察,可缩短传播时间(D)。目前政府采用交通管制、延长企业开工和学校开学时间、取消会议和公众聚会也能够有效、尽快地降低有效再生数。
从目前已经获知信息来看,相当一部分 2019-nCoV 的感染者仅表现为轻微症状,他们原则上具有和健康人一样的活动能力。有一些初期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提示 2019-nCoV 在潜伏期具备一定传染性。再加上武汉出台防控政策时已错过黄金时间,导致 2019-nCoV 的初期传播势头显得比 SARS 还要凶猛。但我们认为,只要按照国家部署和各级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对 2019-nCoV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对疑似患者(包括潜伏期和轻微症)患者进行隔离和治疗,采用“小汤山医院”模式对重症患者进行强化治疗,严防医院感染,做好自我保护,全面减少和其他人的接触,根据我们抗击 SARS 的经验,2019-nCoV 将会很快得到有效控制。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收集 2019-nCoV 在自由传播状态下的病例数据,采用 SEIR 模型预测得到 2019-nCoV 传播初期的基本再生数略高于 SARS 病毒,表明 2019-nCoV 属于中高度传染性的传播疾病。为尽快控制 2019-nCoV 蔓延,需要在切断传染源、降低传染率和缩短传播时间的各环节进行有效防控。此外,本文在预测的过程中,采用了与 SARS 传播初期的相关参数,且发现预测得到的基本再生数对生成时间敏感。未来为了得到更准确的预测结果,还需更多微观传播的数据对模型和参数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