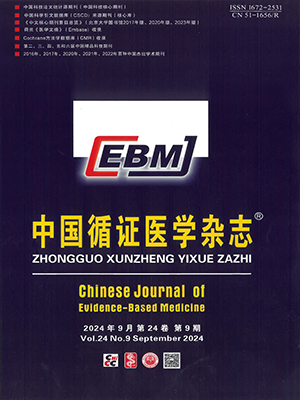累积Meta分析可以有助于研究者做出对干预措施有效/无效的判断,以及所获得的证据是否足够,然而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对重复检验进行校正,也没有关注统计效能。序贯Meta分析的产生使得上述问题得以解决,被广泛应用于循证临床实践和决策。目前有多种序贯Meta分析,不同方法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其中试验序贯分析(TSA)的方法学最为成熟,软件操作也较为简单;Whitehead双三角检验的理论不如TSA完善,且操作也较难;半贝叶斯法则涉及到贝叶斯理论,更不易推广。本文主要对当前的这三种主要的序贯Meta分析方法做一简介。
引用本文: 翁鸿, 武珊珊, 张永刚, 靳英辉, 曹越, 曾宪涛. 序贯Meta分析方法学简介.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6, 16(10): 1216-1220. doi: 10.7507/1672-2531.20160184 复制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的Meta分析被认为是证据的最高级别 [1]。Meta分析采用系统、定量的方法合并多个具有相似性的研究,可增大样本量,增强统计效能,增加效应量的精确度。但由于系统误差(偏倚)和随机误差(机遇)的影响,Meta分析可能会得出假阳性结果或高估干预措施的效应量。此外,Cochrane协作网要求作者每2年对Meta分析进行更新,而随着新研究的纳入,也增加了检验次数,使得随机误差增大 [2]。
累积Meta分析常被用来观察效应量随特定顺序(如发表时间等)变化的趋势,判断当前所获得的证据是否足够,以及新的同一主题的RCT是否应该进行 [3]。但累积Meta分析的过程未能对重复检验进行校正,也不能计算拒绝无效假设的统计检验效能。而重复检验会增加Ⅰ型错误风险 [3]。
序贯Meta分析(sequential meta-analysis,SMA)从整体层面上控制显著性水平α(一般为0.05),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纳入试验,将每纳入的一次试验当做一次期中分析(interim analysis)。当前主要的序贯Meta分析方法有:① 丹麦哥本哈根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小组Wetterslev等 [4]提出的试验序贯分析(trial sequential analysis,TSA);② van der Tweel和Bollen [5]推荐的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③ Higgins等[6]提出的半贝叶斯法。此外,还有Shuster和Neu [7]提出的Pocock法,该方法主要用于前瞻性分析,因此,本文暂不做讨论。这三种主要的方法中,TSA的方法学较为成熟,且哥本哈根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小组为其开发了相应的软件,本团队已对该软件的操作做了相关阐述 [8],因此TSA在Meta分析中的应用最为广泛;后两者由于软件以及方法学等因素,尚未能普及。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本文主要对这几种方法做一简介。
1 序贯Meta分析方法学基础
1.1 序贯试验
序贯试验(sequential trial)又称序贯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由于该设计可以满足带有破坏性和危及安全性的试验要求,其最初被用于军火质量检验。序贯试验可分为开放型和闭锁型,根据目的不同可分为单向和双向序贯试验 [9]。图 1为单向序贯试验的序贯图。
 图1
单向序贯试验的序贯图(x轴为样本数、y轴为有效数)
图1
单向序贯试验的序贯图(x轴为样本数、y轴为有效数)
1.2 成组序贯试验
传统的序贯方法要求受试者逐对进入试验,并且只有当得到该试验结果并统计分析后才可确定结束试验还是继续下一个试验 [10]。当得到试验结果的时间较长时(如数周或数月),这种序贯方法就不适用了。而成组序贯试验(group sequential analysis)可用于得到试验结果的时间较长及整个试验过程中分几个时间段来重复分析试验结果的情况。此外,成组序贯试验不要求受试者必须配对。因此该方法既保留了传统序贯方法的优点又避免其局限性,且正好与期中分析相配合。
该方法首先由Pocock于1977年提出 [11],在国外的药物临床试验中应用较为广泛。在这一分析过程中要进行多次重复显著性检验,而这将增加Ⅰ型错误风险。因此,为使总的显著性水平等于α,Pocock [11]提出了名义显著性水平α',并规定每个阶段检验的名义显著性水平α'小于α。O’Brien和Fleming [12]提出在试验的不同阶段取不同的α',在早期应更严格,并定义检验统计量的方差与累积样本大小成比例。此外,Slud和Wei [13]也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Wilcoxon统计量(渐进高斯分布)的方法。但这些方法都需要提前定义所需时段的次数,也就是分析的次数。Lan和DeMetes [14]于1983年提出了一种更为灵活的离散界值,仅需要提前定义一个单调递增的α损耗函数α*(t),其公式为:
| $\alpha *\left( t \right)=\left\{ \begin{matrix} 0 & \left( t=0 \right) \\ 2\left[ 1-\phi \left\{ {{Z}_{\alpha /2}}/ \right\} \right] & \left( 0\le t\le 1 \right) \\ \end{matrix} \right.$ |
其中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当t=1时,α*(1) =α。
1.3 序贯方法引入累积Meta分析
Pogue和Yusuf [15]于1997年将Lan-DeMetes α损耗函数引入累积Meta分析,用该损耗函数来计算Meta分析的界值,同时提出了最优信息量(optional information size,OIS)的概念。计算OIS需要假设事件发生率和最小干预效果,公式为:
| $N=2\times \frac{{{\left( {{Z}_{\alpha }}+{{Z}_{\beta }} \right)}^{2}}\times 2P*\left( 1-P* \right)}{{{\left( {{P}_{C}}-{{P}_{E}} \right)}^{2}}}$ |
其中P*=(PC+PE)/2,PC、PE分别为对照组和试验组事件发生率,N即为OIS。
2 试验序贯分析(TSA)
丹麦哥本哈根临床试验中心小组将Pogue和Yusuf的方法进行延伸,提出了TSA方法 [16-19],同时提出了期望信息量(required information size,RIS)的概念,并提供了多种用于估算RIS的方法,如累积信息量(accrued information size,AIS)、先验信息量(a priori information size,APIS)、低偏倚信息量(low-bias information size,LBIS)、低偏倚异质性校正信息量(low-bias heterogeneity-adjusted information size,LBHIS)、差异校正信息量(diversity-adjusted information size,DIS)。关于TSA方法,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介绍,本文暂不做相关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王权 [20, 21]、夏芸 [22]、王欢 [23]等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当然,除了TSA软件可以进行TSA界值图的绘制外,其他软件也可以,如Stata、Excel、SAS、R等软件(如图 2、3)。
 图2
Stata绘制的TSA界值图
图2
Stata绘制的TSA界值图
(RRR=25%,
 图3
Excel绘制的TSA界值图
图3
Excel绘制的TSA界值图
(RRR=25%,
3 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
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方法起源于单个原始RCT的研究设计 [24],在单个RCT的序贯分析中,分析的单位是单个病人,不通过α损耗函数来控制显著性水平。Whitehead等 [25-27]将其引入累积Meta分析,分析单位为每一个RCT,也就是一组病人,采用统计量(Z,V)控制总的显著性水平,该方法得到van der Tweel和Bollen的推广 [5]。该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25]:① 无需提前预估总体信息量,设置一组界值即可;② 具有终止无效假设的标准,当然TSA也具有这一特点;③ 可以量化统计效能;④ 点估计和区间估计都可进行多重检验校正;⑤ 可增加效率,即无效/有效假设均有接受的标准,可达到伦理学和经济学上的优化。
在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中,每个RCT具有两个值:Zi和Vi,Zi不同于TSA中的检验统计量。Zi表示累积Meta分析中第i个研究试验组观察到的事件发生数与无效假设下试验组事件期望值的差值,Vi表示表示在无效假设下Zi的方差。数据格式如表 1所示,则相应的Zi和Vi的计算方法为:
| $\begin{align} & {{Z}_{i}}={{F}_{Ei}}-{{N}_{Ei}}{{F}_{i}}/{{N}_{i}}=\frac{{{N}_{CI}}{{F}_{Ei}}-{{N}_{Ei}}{{F}_{CI}}}{{{N}_{i}}} \\ & {{V}_{i}}=\frac{{{N}_{Ei}}{{N}_{CI}}{{S}_{i}}{{F}_{i}}}{N_{i}^{2}\left( {{N}_{i}}-1 \right)} \\ \end{align}$ |
根据表 1数据格式,第i个RCT的效应量ORi= PEi(1-PCi)/[PCi(1-PEi)],定义临床疗效θi=ln(ORi)。在进行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分析前估计相关的临床疗效θR(=lnOR)。
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方法的界值图采用双三角检验方法,由四条线组成,外部上界(U1)、下界(L1)和内部上界(U2)、下界(L2),分别表示为:U1:Z=a+cV;L1:Z=-a-cV;U2:Z=-a+3cV;L2:Z=a-3cV
其中系数a、c由Ⅰ型错误α、Ⅱ型错误β以及相关临床效应θR共同决定。当α/2=β时,效应量δR截距a=(2/δR)log(1/α),斜率c=δR/4,坐标定为V=4a/δR、Z=2a;当α/2≠β时,效应量δR=2Uα/2θR/(Uα/2+Uβ)。若将截距a替换为,则这种校正方法被称为“圣诞树校正” [28]。
如图 4所示,纵轴为Z,横轴为V,绿色线条为U1,蓝色线条为U2,紫色线条为L1,红色线条为L2,若累积的研究坐标(Zi,Vi)超过U1或L1,则拒绝H0,即试验组干预措施优于对照组干预措施;若超过U2或L2,则接受H0,即试验组干预措施与对照组干预措施无差异;若没有超过任何一条界值线,则表明当前的证据尚不足以得出结论,仍需进一步看展相关研究进行验证。
 图4
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界值图
图4
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界值图
4 半贝叶斯法
Higgins等 [6]提出了半贝叶斯法,与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方法不同的是,半贝叶斯法基于(Z,V)平面(此方法的Z和V与上述方法不同),采用对称的Z=±H、V=Vmax边界以及纵轴作为矩形平面,该方法避免了积分计算。
假设估计效应为yi,真实效应为θi,相应的估计方差为vi,i为纳入的研究数(i=1,…,k)。若θi=yi,vi=0,则倒γ先验分布的异质性方差τ2与未知正态分布的方差共轭,且τ2与的后验分布也为倒γ分布,那么纳入tj(若开始纳入研究数为2,则t1=2)个研究间的异质性方差为(其参数为η+(tj/2) 、λ+(tjτj2/2) ),采用DerSimonian-Laird法估计的方差为,则τ2的后验均数为:
| ${{{\hat{\tau }}}^{2}}_{AB,j}=\frac{2\lambda +{{t}_{j}}\hat{\tau }_{DL,j}^{2}}{2\eta +{{t}_{j}}-2}=\frac{2\left( \eta -1 \right){{{\hat{\tau }}}^{2}}_{AB,0}+{{t}_{j}}\hat{\tau }_{DL,j}^{2}}{2\left( \eta -1 \right)+{{t}_{j}}}$ |
其中是先验倒γ分布的均值。则后验均值可被认为为τ2先验估计的加权平均数,随着纳入研究数量的增加,先验信息递减。在随机效应模型下,半贝叶斯法的Zj、Vj计算方法如下:
| ${{Z}_{j}}=\sum\nolimits_{i=1}^{{{t}_{j}}}{W_{AB,i}^{*}}{{Y}_{i}},{{V}_{j}}=\sum\nolimits_{i=1}^{{{t}_{j}}}{W}_{AB,i}^{*}$ |
其中,当纳入研究够多(即yi≈θi,vi=0)时,以及纳入研究较少而导致高估τ2(与θi分布相比较,yi估计值的分布过度离散)时,该方法可以得到较好的结果。
5 小结
虽然序贯分析在单个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Meta分析领域的应用仍不广泛。有学者认为Meta分析不能控制新证据的产生,不能扮演终止标准,因此不能使用序贯方法,而Higgins等 [6]认为Meta分析常用于决策或检验某一干预措施当前是否存在最佳可信的证据,此外Meta分析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合理的建议,而不是直接控制未来的研究,因此序贯分析方法对Meta分析的重要性等同于其对单个研究的重要性。
Brok等 [29]研究表明许多表面上已经明确的Meta分析结论可能是不明确的,他们分析了54篇具有阳性结果的Cochran新生儿方面的Meta分析,发现有39篇(72%)Meta分析没有达到异质性校正信息量;这39篇Meta分析中,有19篇(49%)Meta分析的结论是不确定的。因此SMA可以较为完善地解决累积Meta分析的弊端,即重复检验造成的假阳性结果发生率增大,不仅提供了有效的终止标准,也提供了无效的终止标准。
但是,SMA的方法仍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TSA虽然发展较为迅速,但该方法估算信息量的方法有多种,有一定的差异,需要根据具体的文献质量情况进行选择,此外对相对危险度的估计也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研究者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才能正确的进行估算。此外,Kulinskaya和Wood指出,TSA仅考虑了研究信息量,而没有考虑研究数量,并指出TSA在随机效应Meta分析下的计算具有弊端 [30]。而其他方法由于方法学繁琐及没有便捷的操作软件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难以推广应用。
我们推荐研究者在制作Meta分析时采用序贯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进行适当选择。制作SMA,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读者对该Meta分析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的Meta分析被认为是证据的最高级别 [1]。Meta分析采用系统、定量的方法合并多个具有相似性的研究,可增大样本量,增强统计效能,增加效应量的精确度。但由于系统误差(偏倚)和随机误差(机遇)的影响,Meta分析可能会得出假阳性结果或高估干预措施的效应量。此外,Cochrane协作网要求作者每2年对Meta分析进行更新,而随着新研究的纳入,也增加了检验次数,使得随机误差增大 [2]。
累积Meta分析常被用来观察效应量随特定顺序(如发表时间等)变化的趋势,判断当前所获得的证据是否足够,以及新的同一主题的RCT是否应该进行 [3]。但累积Meta分析的过程未能对重复检验进行校正,也不能计算拒绝无效假设的统计检验效能。而重复检验会增加Ⅰ型错误风险 [3]。
序贯Meta分析(sequential meta-analysis,SMA)从整体层面上控制显著性水平α(一般为0.05),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纳入试验,将每纳入的一次试验当做一次期中分析(interim analysis)。当前主要的序贯Meta分析方法有:① 丹麦哥本哈根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小组Wetterslev等 [4]提出的试验序贯分析(trial sequential analysis,TSA);② van der Tweel和Bollen [5]推荐的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③ Higgins等[6]提出的半贝叶斯法。此外,还有Shuster和Neu [7]提出的Pocock法,该方法主要用于前瞻性分析,因此,本文暂不做讨论。这三种主要的方法中,TSA的方法学较为成熟,且哥本哈根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小组为其开发了相应的软件,本团队已对该软件的操作做了相关阐述 [8],因此TSA在Meta分析中的应用最为广泛;后两者由于软件以及方法学等因素,尚未能普及。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本文主要对这几种方法做一简介。
1 序贯Meta分析方法学基础
1.1 序贯试验
序贯试验(sequential trial)又称序贯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由于该设计可以满足带有破坏性和危及安全性的试验要求,其最初被用于军火质量检验。序贯试验可分为开放型和闭锁型,根据目的不同可分为单向和双向序贯试验 [9]。图 1为单向序贯试验的序贯图。
 图1
单向序贯试验的序贯图(x轴为样本数、y轴为有效数)
图1
单向序贯试验的序贯图(x轴为样本数、y轴为有效数)
1.2 成组序贯试验
传统的序贯方法要求受试者逐对进入试验,并且只有当得到该试验结果并统计分析后才可确定结束试验还是继续下一个试验 [10]。当得到试验结果的时间较长时(如数周或数月),这种序贯方法就不适用了。而成组序贯试验(group sequential analysis)可用于得到试验结果的时间较长及整个试验过程中分几个时间段来重复分析试验结果的情况。此外,成组序贯试验不要求受试者必须配对。因此该方法既保留了传统序贯方法的优点又避免其局限性,且正好与期中分析相配合。
该方法首先由Pocock于1977年提出 [11],在国外的药物临床试验中应用较为广泛。在这一分析过程中要进行多次重复显著性检验,而这将增加Ⅰ型错误风险。因此,为使总的显著性水平等于α,Pocock [11]提出了名义显著性水平α',并规定每个阶段检验的名义显著性水平α'小于α。O’Brien和Fleming [12]提出在试验的不同阶段取不同的α',在早期应更严格,并定义检验统计量的方差与累积样本大小成比例。此外,Slud和Wei [13]也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Wilcoxon统计量(渐进高斯分布)的方法。但这些方法都需要提前定义所需时段的次数,也就是分析的次数。Lan和DeMetes [14]于1983年提出了一种更为灵活的离散界值,仅需要提前定义一个单调递增的α损耗函数α*(t),其公式为:
| $\alpha *\left( t \right)=\left\{ \begin{matrix} 0 & \left( t=0 \right) \\ 2\left[ 1-\phi \left\{ {{Z}_{\alpha /2}}/ \right\} \right] & \left( 0\le t\le 1 \right) \\ \end{matrix} \right.$ |
其中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当t=1时,α*(1) =α。
1.3 序贯方法引入累积Meta分析
Pogue和Yusuf [15]于1997年将Lan-DeMetes α损耗函数引入累积Meta分析,用该损耗函数来计算Meta分析的界值,同时提出了最优信息量(optional information size,OIS)的概念。计算OIS需要假设事件发生率和最小干预效果,公式为:
| $N=2\times \frac{{{\left( {{Z}_{\alpha }}+{{Z}_{\beta }} \right)}^{2}}\times 2P*\left( 1-P* \right)}{{{\left( {{P}_{C}}-{{P}_{E}} \right)}^{2}}}$ |
其中P*=(PC+PE)/2,PC、PE分别为对照组和试验组事件发生率,N即为OIS。
2 试验序贯分析(TSA)
丹麦哥本哈根临床试验中心小组将Pogue和Yusuf的方法进行延伸,提出了TSA方法 [16-19],同时提出了期望信息量(required information size,RIS)的概念,并提供了多种用于估算RIS的方法,如累积信息量(accrued information size,AIS)、先验信息量(a priori information size,APIS)、低偏倚信息量(low-bias information size,LBIS)、低偏倚异质性校正信息量(low-bias heterogeneity-adjusted information size,LBHIS)、差异校正信息量(diversity-adjusted information size,DIS)。关于TSA方法,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介绍,本文暂不做相关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王权 [20, 21]、夏芸 [22]、王欢 [23]等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当然,除了TSA软件可以进行TSA界值图的绘制外,其他软件也可以,如Stata、Excel、SAS、R等软件(如图 2、3)。
 图2
Stata绘制的TSA界值图
图2
Stata绘制的TSA界值图
(RRR=25%,
 图3
Excel绘制的TSA界值图
图3
Excel绘制的TSA界值图
(RRR=25%,
3 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
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方法起源于单个原始RCT的研究设计 [24],在单个RCT的序贯分析中,分析的单位是单个病人,不通过α损耗函数来控制显著性水平。Whitehead等 [25-27]将其引入累积Meta分析,分析单位为每一个RCT,也就是一组病人,采用统计量(Z,V)控制总的显著性水平,该方法得到van der Tweel和Bollen的推广 [5]。该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25]:① 无需提前预估总体信息量,设置一组界值即可;② 具有终止无效假设的标准,当然TSA也具有这一特点;③ 可以量化统计效能;④ 点估计和区间估计都可进行多重检验校正;⑤ 可增加效率,即无效/有效假设均有接受的标准,可达到伦理学和经济学上的优化。
在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中,每个RCT具有两个值:Zi和Vi,Zi不同于TSA中的检验统计量。Zi表示累积Meta分析中第i个研究试验组观察到的事件发生数与无效假设下试验组事件期望值的差值,Vi表示表示在无效假设下Zi的方差。数据格式如表 1所示,则相应的Zi和Vi的计算方法为:
| $\begin{align} & {{Z}_{i}}={{F}_{Ei}}-{{N}_{Ei}}{{F}_{i}}/{{N}_{i}}=\frac{{{N}_{CI}}{{F}_{Ei}}-{{N}_{Ei}}{{F}_{CI}}}{{{N}_{i}}} \\ & {{V}_{i}}=\frac{{{N}_{Ei}}{{N}_{CI}}{{S}_{i}}{{F}_{i}}}{N_{i}^{2}\left( {{N}_{i}}-1 \right)} \\ \end{align}$ |
根据表 1数据格式,第i个RCT的效应量ORi= PEi(1-PCi)/[PCi(1-PEi)],定义临床疗效θi=ln(ORi)。在进行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分析前估计相关的临床疗效θR(=lnOR)。
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方法的界值图采用双三角检验方法,由四条线组成,外部上界(U1)、下界(L1)和内部上界(U2)、下界(L2),分别表示为:U1:Z=a+cV;L1:Z=-a-cV;U2:Z=-a+3cV;L2:Z=a-3cV
其中系数a、c由Ⅰ型错误α、Ⅱ型错误β以及相关临床效应θR共同决定。当α/2=β时,效应量δR截距a=(2/δR)log(1/α),斜率c=δR/4,坐标定为V=4a/δR、Z=2a;当α/2≠β时,效应量δR=2Uα/2θR/(Uα/2+Uβ)。若将截距a替换为,则这种校正方法被称为“圣诞树校正” [28]。
如图 4所示,纵轴为Z,横轴为V,绿色线条为U1,蓝色线条为U2,紫色线条为L1,红色线条为L2,若累积的研究坐标(Zi,Vi)超过U1或L1,则拒绝H0,即试验组干预措施优于对照组干预措施;若超过U2或L2,则接受H0,即试验组干预措施与对照组干预措施无差异;若没有超过任何一条界值线,则表明当前的证据尚不足以得出结论,仍需进一步看展相关研究进行验证。
 图4
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界值图
图4
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界值图
4 半贝叶斯法
Higgins等 [6]提出了半贝叶斯法,与Whitehead双三角检验SMA方法不同的是,半贝叶斯法基于(Z,V)平面(此方法的Z和V与上述方法不同),采用对称的Z=±H、V=Vmax边界以及纵轴作为矩形平面,该方法避免了积分计算。
假设估计效应为yi,真实效应为θi,相应的估计方差为vi,i为纳入的研究数(i=1,…,k)。若θi=yi,vi=0,则倒γ先验分布的异质性方差τ2与未知正态分布的方差共轭,且τ2与的后验分布也为倒γ分布,那么纳入tj(若开始纳入研究数为2,则t1=2)个研究间的异质性方差为(其参数为η+(tj/2) 、λ+(tjτj2/2) ),采用DerSimonian-Laird法估计的方差为,则τ2的后验均数为:
| ${{{\hat{\tau }}}^{2}}_{AB,j}=\frac{2\lambda +{{t}_{j}}\hat{\tau }_{DL,j}^{2}}{2\eta +{{t}_{j}}-2}=\frac{2\left( \eta -1 \right){{{\hat{\tau }}}^{2}}_{AB,0}+{{t}_{j}}\hat{\tau }_{DL,j}^{2}}{2\left( \eta -1 \right)+{{t}_{j}}}$ |
其中是先验倒γ分布的均值。则后验均值可被认为为τ2先验估计的加权平均数,随着纳入研究数量的增加,先验信息递减。在随机效应模型下,半贝叶斯法的Zj、Vj计算方法如下:
| ${{Z}_{j}}=\sum\nolimits_{i=1}^{{{t}_{j}}}{W_{AB,i}^{*}}{{Y}_{i}},{{V}_{j}}=\sum\nolimits_{i=1}^{{{t}_{j}}}{W}_{AB,i}^{*}$ |
其中,当纳入研究够多(即yi≈θi,vi=0)时,以及纳入研究较少而导致高估τ2(与θi分布相比较,yi估计值的分布过度离散)时,该方法可以得到较好的结果。
5 小结
虽然序贯分析在单个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Meta分析领域的应用仍不广泛。有学者认为Meta分析不能控制新证据的产生,不能扮演终止标准,因此不能使用序贯方法,而Higgins等 [6]认为Meta分析常用于决策或检验某一干预措施当前是否存在最佳可信的证据,此外Meta分析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合理的建议,而不是直接控制未来的研究,因此序贯分析方法对Meta分析的重要性等同于其对单个研究的重要性。
Brok等 [29]研究表明许多表面上已经明确的Meta分析结论可能是不明确的,他们分析了54篇具有阳性结果的Cochran新生儿方面的Meta分析,发现有39篇(72%)Meta分析没有达到异质性校正信息量;这39篇Meta分析中,有19篇(49%)Meta分析的结论是不确定的。因此SMA可以较为完善地解决累积Meta分析的弊端,即重复检验造成的假阳性结果发生率增大,不仅提供了有效的终止标准,也提供了无效的终止标准。
但是,SMA的方法仍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TSA虽然发展较为迅速,但该方法估算信息量的方法有多种,有一定的差异,需要根据具体的文献质量情况进行选择,此外对相对危险度的估计也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研究者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才能正确的进行估算。此外,Kulinskaya和Wood指出,TSA仅考虑了研究信息量,而没有考虑研究数量,并指出TSA在随机效应Meta分析下的计算具有弊端 [30]。而其他方法由于方法学繁琐及没有便捷的操作软件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难以推广应用。
我们推荐研究者在制作Meta分析时采用序贯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进行适当选择。制作SMA,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读者对该Meta分析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