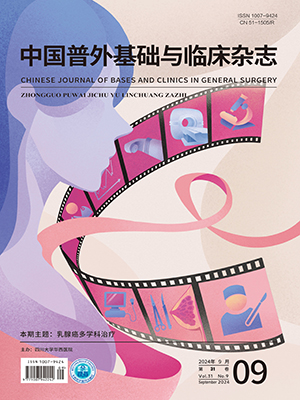引用本文: 陈熙, 胡朝辉, 彭永海, 罗华. 腹腔镜肝切除术后不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的疗效分析.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20, 27(9): 1089-1093. doi: 10.7507/1007-9424.202005030 复制
腹腔镜肝切除具有创伤小、出血少、住院时间短等特点,临床开展日益增多[1]。尤其是近年来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的引入,进一步缩短了腹腔镜肝切除患者的住院时间[2]。腹腔镜肝切除术后是否需要常规放置引流管,目前尚未能达成共识,国内亦无相关临床研究支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表明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3]、胃癌根治术[4]、结肠癌术[5]后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并不能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或改变预后,反而可能会增加腹腔逆行性感染的风险。本研究探讨了在腹腔镜肝切除术后不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的疗效及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收集 2019 年 6 月至 12 月期间因肝脏肿瘤在我院行腹腔镜肝切除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纳入标准:① 因原发性肝细胞癌、结肠癌肝转移或肝血管瘤行腹腔镜肝切除患者;② Child-Pugh 评分 A、B 级;③ 吲哚菁绿 15 min 滞留率(indocyanine green retention rate at 15 min,ICGR15)<20%;④ 心肺功能能够耐受手术;⑤ 临床病理资料完善。排除标准:① 胆管细胞肝癌、肝门胆管癌需要行淋巴结清扫的患者;② 因文献[6-7]报道肝中叶切除术后胆汁漏发生率明显增高,我中心肝中叶切除术后均常规放置了腹腔引流管,为保证 2 组基线均衡,肝中叶切除患者不纳入研究分析,包括 Ⅴ 段、Ⅳb 段、Ⅴ+Ⅳb 段、Ⅴ+Ⅳ+Ⅷ 段;③ 联合胆道探查或胆肠吻合术患者;④ 联合脏器切除患者。
1.2 手术方法
患者围手术期处理均按照 2017 年腹腔镜肝切除术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进行[2]。腹腔镜肝切除采用 5 孔法,气腹压力 14~15 mm Hg(1 mm Hg=0.133 kPa)。中心静脉压维持在 5 mm H2O(1 mm H2O=0.098 kPa)以下。肝切除范围取决于术前影像学检查、术中超声定位情况。肝门阻断采用间断 Pringle 法,每次阻断 15 min,开放 5 min。肝实质离断使用超声刀或 LigaSure 配合钛夹、Hem-o-lock 进行。肝蒂及肝静脉离断用切割闭合器。肝断面常规使用百克钳烧灼后,白色纱布仔细擦拭断面,查看有无黄染,若有黄染仔细查看断面漏胆处,使用血管线连续缝合。断面常规覆盖速即纱。是否放置腹腔引流管根据术前患方家属知情签署的同意书决定。
1.3 术后管理
术后治疗包括镇痛、止吐、抑制胃酸分泌、保肝、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镇痛模式采用硬膜外罗哌卡因持续泵入联合定时静脉注射 COX-2 抑制剂。术后常规给予止吐药物,麻醉清醒即可饮水,术后第 1 天鼓励患者进流质饮食。1~2 d 鼓励患者下床活动。术后每天行床旁超声检查,了解腹腔积液情况。当出现腹膜炎表现怀疑胆汁漏或心率突然加快、血压下降等失血性休克表现时应及时行腹腔穿刺及其他相关实验室检查以明确诊断。置管组术后第 3 天排除腹腔感染及胆汁漏后拔除腹腔引流管。当患者术后 3 d 胆红素<50 μmol/L 且持续下降、凝血功能无明显异常、无感染表现时即可出院。
1.4 评价标准
肝脏切除术式的命名规则按照布里斯班标准[8]。术后腹腔出血诊断标准为:腹腔出血需要输入红细胞悬液或再次手术止血。胆漏诊断标准[9]为:术后第 3 天腹水中总胆红素水平大于血清总胆红素水平 3 倍。术后腹腔感染诊断标准[10]为:出现腹膜炎表现且引流液中细菌培养阳性(未置管组不常规行腹水检查,仅当出现腹膜炎表现时才进行诊断性腹腔穿刺并送生化检查)。术后肝功能衰竭诊断标准[11]:采用国际肝脏外科学组提出的 B、C 级肝功能衰竭诊断标准。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使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且 2 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范围)表示且 2 组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 α=0.05。
±s)表示且 2 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范围)表示且 2 组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本研究纳入患者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符合条件的患者 117 例中男 71 例,女 46 例;年龄 28~78 岁、(56±12)岁;未放置引流管组(简称“未置管组”)59 例,放置引流管组(简称“置管组”)58 例;其中肝癌患者 84 例(未置管 44 例,置管 40 例),非肝癌患者 33 例(未置管 15 例,置管 18 例)。
2.2 腹腔镜肝切除术后放置引流管和未放置引流管的结果比较
2.2.1 总体患者
① 置管组和未置管组患者在基线资料如性别、年龄、乙肝病毒感染、体质量指数(BMI)、总胆红素(TBIL)、白蛋白(Alb)、血小板计数(PL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Child A 级、ICGR15、肝硬度值、Ishak 评分、肿瘤最大直径及疾病类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② 置管组和未置管组患者术中及术后相关情况:未置管组较置管组下床活动时间和肛门排气时间均更早(P<0.001)、术后住院时间更短(P=0.030),但 2 组患者的手术方式、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术中出血量、输血、术后并发症及术后需要超声穿刺引流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4 例腹腔出血患者中 2 例行再次手术止血,2 例通过保守治疗治愈;13 例胆汁漏患者均经过保守治疗或超声引导下穿刺引流治愈;4 例腹腔感染患者经过抗感染、超声穿刺引流治愈,无再次手术病例;2 例肝功能衰竭患者给予保肝、纠正凝血等治疗治愈。本组病例无围手术期死亡。
2.2.2 肝癌患者
未置管组较置管组下床活动时间和肛门排气时间更早(P<0.001),而 2 组患者的手术方式、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术中出血量、输血、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及术后需要超声穿刺引流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2.3 非肝癌患者
未置管组较置管组下床活动时间和肛门排气时间更早(P<0.001)、术后住院时间更短(P=0.042),而 2 组患者的手术方式、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术中出血量、输血、术后并发症及术后需要超声穿刺引流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3 讨论
既往认为,腹腔镜肝切除术后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可以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通过对腹水性状的观察从而早期诊断术后腹腔内出血、胆汁漏等并发症并进行积极治疗。然而随着外科学理念的进步,目前是否需要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存在争议[12]。多个临床研究[13-14]表明,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并不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也不能改善并发症发生后的结局;此外,腹腔引流还有导致逆行感染、肠管损伤以及腹水过度丢失的风险[15]。不放置引流管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减轻术后疼痛,使患者更早地下床活动,加速康复[16]。
在本研究中,在未置管组以及置管组各有 2 例出现术后腹腔出血(P=1.000),均表现为突发腹痛、大汗、心率增快、合并或不合并血压下降,在置管组中,有 1 例腹腔出血患者由于引流管被堵塞,也未见大量血性液体流出,行床旁超声检查提示腹腔积液,进一步腹腔穿刺抽出血性液体才最终明确诊断,提示术后腹腔出血的诊断主要依靠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血常规变化及床旁超声检查,而并不能单纯依靠腹腔引流进行判断,通过引流液判断是否发生术后腹腔出血并不可靠。
胆汁漏是肝切除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文献[17]报道其发生率为 13.5%~30.6%。胆汁漏在临床上虽然常见,但多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目前很少因单纯胆汁漏而需要再次手术的病例。随着超声介入技术的进步,超声引导下的腹腔穿刺置管引流具有精准、安全、微创的特点,通常能够有效地处理胆汁漏。胆汁漏患者主要出现反复发热、腹胀、腹部散在压痛、白细胞升高,通过腹腔穿刺抽出胆汁样液体明确诊断。在本研究中,在未置管组以及置管组分别有 6 和 7 例术后发生胆汁漏(P=0.774),同时本研究发现即便术后安置腹腔引流管的患者也有 3 例因胆汁漏需要超声介入的情况,提示即便安置了腹腔引流管也可能因为术后引流管堵塞、过早拔管等因素影响导致需要超声穿刺引流的可能,这与 Wada 等[18]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腹腔镜肝切除如不涉及胆道操作,通常被认为是清洁手术,腹腔感染发生率非常低。腹腔感染主要发生在术后 4 d[19],目前提倡早期拔除腹腔引流管。笔者医疗中心一般拔除腹腔引流管的时间通常在 3~4 d,因此,常规腹腔引流管对于治疗术后防治腹腔感染的有效性较低。
Shwaartz 等[20]在对肝切除病例进行研究发现,不安置腹腔引流管可以显著缩短患者住院时间(P<0.001)且与任何术后并发症发生无关,本研究也发现与此基本一致的结论。分析其原因,不安置腹腔镜引流管能减轻患者切口疼痛,提升患者心理接受度,减少不必要的腹水丢失,促进患者更早下床活动,促进胃肠功能康复,从而缩短住院时间。但在本研究的亚组分析中的结果提示,肝癌患者并未因未安置腹腔引流管而显著缩短住院时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术后恢复与患者的肝脏功能、肝硬化程度及残余肝脏的代偿能力密切相关。由于我国肝癌病例多合并有肝硬化,肝硬化患者术后肝脏再生能力较差[21],肝切除对其全身影响较大,故术后住院时延长的影响因素较非肝癌患者明显增加。
近年来,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及腹腔镜肝切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围手术期管理的优化及治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何在提高疗效的同时减轻患者痛苦、减少医疗费用支出、缩短住院时间,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追求,也是医疗改革的方向。本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在技术娴熟的腹腔镜肝切除中心,术后有选择性地不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并不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同时可以更快地促进患者康复,最大程度地缩短住院时间,符合当代外科发展的方向。但本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如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样本量较少,可能存在一些选择性偏倚,手术的主刀医生不同,无法完全避免因手术技术的高低导致结果差异,期待今后展开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对照研究。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阅读并理解了《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的政策声明,我们无相互竞争的利益。
作者贡献声明:罗华设计了课题;胡朝晖、彭永海、罗华收集、整理数据;陈熙分析数据并撰写了文章。
伦理声明:本研究通过了绵阳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文编号:S20190228)。
腹腔镜肝切除具有创伤小、出血少、住院时间短等特点,临床开展日益增多[1]。尤其是近年来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的引入,进一步缩短了腹腔镜肝切除患者的住院时间[2]。腹腔镜肝切除术后是否需要常规放置引流管,目前尚未能达成共识,国内亦无相关临床研究支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表明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3]、胃癌根治术[4]、结肠癌术[5]后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并不能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或改变预后,反而可能会增加腹腔逆行性感染的风险。本研究探讨了在腹腔镜肝切除术后不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的疗效及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收集 2019 年 6 月至 12 月期间因肝脏肿瘤在我院行腹腔镜肝切除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纳入标准:① 因原发性肝细胞癌、结肠癌肝转移或肝血管瘤行腹腔镜肝切除患者;② Child-Pugh 评分 A、B 级;③ 吲哚菁绿 15 min 滞留率(indocyanine green retention rate at 15 min,ICGR15)<20%;④ 心肺功能能够耐受手术;⑤ 临床病理资料完善。排除标准:① 胆管细胞肝癌、肝门胆管癌需要行淋巴结清扫的患者;② 因文献[6-7]报道肝中叶切除术后胆汁漏发生率明显增高,我中心肝中叶切除术后均常规放置了腹腔引流管,为保证 2 组基线均衡,肝中叶切除患者不纳入研究分析,包括 Ⅴ 段、Ⅳb 段、Ⅴ+Ⅳb 段、Ⅴ+Ⅳ+Ⅷ 段;③ 联合胆道探查或胆肠吻合术患者;④ 联合脏器切除患者。
1.2 手术方法
患者围手术期处理均按照 2017 年腹腔镜肝切除术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进行[2]。腹腔镜肝切除采用 5 孔法,气腹压力 14~15 mm Hg(1 mm Hg=0.133 kPa)。中心静脉压维持在 5 mm H2O(1 mm H2O=0.098 kPa)以下。肝切除范围取决于术前影像学检查、术中超声定位情况。肝门阻断采用间断 Pringle 法,每次阻断 15 min,开放 5 min。肝实质离断使用超声刀或 LigaSure 配合钛夹、Hem-o-lock 进行。肝蒂及肝静脉离断用切割闭合器。肝断面常规使用百克钳烧灼后,白色纱布仔细擦拭断面,查看有无黄染,若有黄染仔细查看断面漏胆处,使用血管线连续缝合。断面常规覆盖速即纱。是否放置腹腔引流管根据术前患方家属知情签署的同意书决定。
1.3 术后管理
术后治疗包括镇痛、止吐、抑制胃酸分泌、保肝、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镇痛模式采用硬膜外罗哌卡因持续泵入联合定时静脉注射 COX-2 抑制剂。术后常规给予止吐药物,麻醉清醒即可饮水,术后第 1 天鼓励患者进流质饮食。1~2 d 鼓励患者下床活动。术后每天行床旁超声检查,了解腹腔积液情况。当出现腹膜炎表现怀疑胆汁漏或心率突然加快、血压下降等失血性休克表现时应及时行腹腔穿刺及其他相关实验室检查以明确诊断。置管组术后第 3 天排除腹腔感染及胆汁漏后拔除腹腔引流管。当患者术后 3 d 胆红素<50 μmol/L 且持续下降、凝血功能无明显异常、无感染表现时即可出院。
1.4 评价标准
肝脏切除术式的命名规则按照布里斯班标准[8]。术后腹腔出血诊断标准为:腹腔出血需要输入红细胞悬液或再次手术止血。胆漏诊断标准[9]为:术后第 3 天腹水中总胆红素水平大于血清总胆红素水平 3 倍。术后腹腔感染诊断标准[10]为:出现腹膜炎表现且引流液中细菌培养阳性(未置管组不常规行腹水检查,仅当出现腹膜炎表现时才进行诊断性腹腔穿刺并送生化检查)。术后肝功能衰竭诊断标准[11]:采用国际肝脏外科学组提出的 B、C 级肝功能衰竭诊断标准。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使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且 2 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范围)表示且 2 组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 α=0.05。
±s)表示且 2 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范围)表示且 2 组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本研究纳入患者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符合条件的患者 117 例中男 71 例,女 46 例;年龄 28~78 岁、(56±12)岁;未放置引流管组(简称“未置管组”)59 例,放置引流管组(简称“置管组”)58 例;其中肝癌患者 84 例(未置管 44 例,置管 40 例),非肝癌患者 33 例(未置管 15 例,置管 18 例)。
2.2 腹腔镜肝切除术后放置引流管和未放置引流管的结果比较
2.2.1 总体患者
① 置管组和未置管组患者在基线资料如性别、年龄、乙肝病毒感染、体质量指数(BMI)、总胆红素(TBIL)、白蛋白(Alb)、血小板计数(PL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Child A 级、ICGR15、肝硬度值、Ishak 评分、肿瘤最大直径及疾病类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② 置管组和未置管组患者术中及术后相关情况:未置管组较置管组下床活动时间和肛门排气时间均更早(P<0.001)、术后住院时间更短(P=0.030),但 2 组患者的手术方式、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术中出血量、输血、术后并发症及术后需要超声穿刺引流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4 例腹腔出血患者中 2 例行再次手术止血,2 例通过保守治疗治愈;13 例胆汁漏患者均经过保守治疗或超声引导下穿刺引流治愈;4 例腹腔感染患者经过抗感染、超声穿刺引流治愈,无再次手术病例;2 例肝功能衰竭患者给予保肝、纠正凝血等治疗治愈。本组病例无围手术期死亡。
2.2.2 肝癌患者
未置管组较置管组下床活动时间和肛门排气时间更早(P<0.001),而 2 组患者的手术方式、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术中出血量、输血、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及术后需要超声穿刺引流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2.3 非肝癌患者
未置管组较置管组下床活动时间和肛门排气时间更早(P<0.001)、术后住院时间更短(P=0.042),而 2 组患者的手术方式、手术时间、肝门阻断时间、术中出血量、输血、术后并发症及术后需要超声穿刺引流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3 讨论
既往认为,腹腔镜肝切除术后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可以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通过对腹水性状的观察从而早期诊断术后腹腔内出血、胆汁漏等并发症并进行积极治疗。然而随着外科学理念的进步,目前是否需要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存在争议[12]。多个临床研究[13-14]表明,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并不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也不能改善并发症发生后的结局;此外,腹腔引流还有导致逆行感染、肠管损伤以及腹水过度丢失的风险[15]。不放置引流管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减轻术后疼痛,使患者更早地下床活动,加速康复[16]。
在本研究中,在未置管组以及置管组各有 2 例出现术后腹腔出血(P=1.000),均表现为突发腹痛、大汗、心率增快、合并或不合并血压下降,在置管组中,有 1 例腹腔出血患者由于引流管被堵塞,也未见大量血性液体流出,行床旁超声检查提示腹腔积液,进一步腹腔穿刺抽出血性液体才最终明确诊断,提示术后腹腔出血的诊断主要依靠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血常规变化及床旁超声检查,而并不能单纯依靠腹腔引流进行判断,通过引流液判断是否发生术后腹腔出血并不可靠。
胆汁漏是肝切除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文献[17]报道其发生率为 13.5%~30.6%。胆汁漏在临床上虽然常见,但多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目前很少因单纯胆汁漏而需要再次手术的病例。随着超声介入技术的进步,超声引导下的腹腔穿刺置管引流具有精准、安全、微创的特点,通常能够有效地处理胆汁漏。胆汁漏患者主要出现反复发热、腹胀、腹部散在压痛、白细胞升高,通过腹腔穿刺抽出胆汁样液体明确诊断。在本研究中,在未置管组以及置管组分别有 6 和 7 例术后发生胆汁漏(P=0.774),同时本研究发现即便术后安置腹腔引流管的患者也有 3 例因胆汁漏需要超声介入的情况,提示即便安置了腹腔引流管也可能因为术后引流管堵塞、过早拔管等因素影响导致需要超声穿刺引流的可能,这与 Wada 等[18]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腹腔镜肝切除如不涉及胆道操作,通常被认为是清洁手术,腹腔感染发生率非常低。腹腔感染主要发生在术后 4 d[19],目前提倡早期拔除腹腔引流管。笔者医疗中心一般拔除腹腔引流管的时间通常在 3~4 d,因此,常规腹腔引流管对于治疗术后防治腹腔感染的有效性较低。
Shwaartz 等[20]在对肝切除病例进行研究发现,不安置腹腔引流管可以显著缩短患者住院时间(P<0.001)且与任何术后并发症发生无关,本研究也发现与此基本一致的结论。分析其原因,不安置腹腔镜引流管能减轻患者切口疼痛,提升患者心理接受度,减少不必要的腹水丢失,促进患者更早下床活动,促进胃肠功能康复,从而缩短住院时间。但在本研究的亚组分析中的结果提示,肝癌患者并未因未安置腹腔引流管而显著缩短住院时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术后恢复与患者的肝脏功能、肝硬化程度及残余肝脏的代偿能力密切相关。由于我国肝癌病例多合并有肝硬化,肝硬化患者术后肝脏再生能力较差[21],肝切除对其全身影响较大,故术后住院时延长的影响因素较非肝癌患者明显增加。
近年来,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及腹腔镜肝切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围手术期管理的优化及治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何在提高疗效的同时减轻患者痛苦、减少医疗费用支出、缩短住院时间,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追求,也是医疗改革的方向。本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在技术娴熟的腹腔镜肝切除中心,术后有选择性地不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并不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同时可以更快地促进患者康复,最大程度地缩短住院时间,符合当代外科发展的方向。但本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如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样本量较少,可能存在一些选择性偏倚,手术的主刀医生不同,无法完全避免因手术技术的高低导致结果差异,期待今后展开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对照研究。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阅读并理解了《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的政策声明,我们无相互竞争的利益。
作者贡献声明:罗华设计了课题;胡朝晖、彭永海、罗华收集、整理数据;陈熙分析数据并撰写了文章。
伦理声明:本研究通过了绵阳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文编号:S2019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