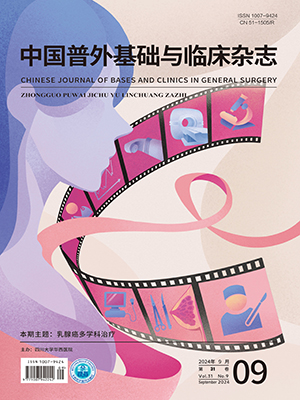引用本文: 李斌, 姜小清. 胆囊癌的规范化手术治疗.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9, 26(3): 265-269. doi: 10.7507/1007-9424.201902073 复制
胆囊癌起源于胆囊底部、体部、颈部或胆囊管,是恶性程度极高的消化系统上皮性肿瘤。回顾胆囊癌包括手术、放疗、化疗、肿瘤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手段的进展,目前胆囊癌的预后仍令人失望。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国际抗癌联盟(AJCC/UICC)对美国 1989–1996 年诊断为胆囊癌的 10 705 例患者进行了随访 5 年以上的研究,证实随着肿瘤进展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人群 5 年生存率由 AJCC/UICC TNM 分期(第 7 版)[1]Ⅰ期的 50%,降至Ⅳa 期的 4%、Ⅳb 期的 2%[2]。因此,在胆囊癌仍缺乏有效的综合治疗的当下,对胆囊癌流行病学危险因素的有效管控,是防范其发生最为有效的措施。
胆囊结石是胆囊癌的首要风险因素(图 1a、1b)[3-6]。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作为一种特殊的胆囊慢性炎症,是胆囊的癌前病变(图 1c、1d)。此外,合并胆胰管汇合异常及胆管囊状扩张症会导致胆囊长期处于炎症状态,亦是胆囊癌的危险因素(图 1e)[7-8]。对上述胆囊癌癌前病变的危害性及其规范化治疗,应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
 图1
示不同情况胆囊癌手术切除标本或影像学照片
图1
示不同情况胆囊癌手术切除标本或影像学照片
a、b:示胆囊结石癌变病例手术切除标本,见胆囊结石、胆囊癌,肿瘤侵及胆囊床肝组织。c、d:示胆囊癌合并黄色肉芽肿,MRI(c)显示胆囊壁显著增厚,胆囊腔内实性占位病灶(红色星号),胆囊外壁尚光滑,胆囊周围肝组织未受肿瘤侵犯,胰头后方淋巴结肿大(黄色箭头);胆囊剖检(d):见胆囊底部及体部黄色肉芽肿(黑色星号),合并胆囊颈部腺癌(白色星号),肿瘤于胆囊腔内生长,未突破胆囊浆膜层。e:示先天性胆管囊状扩张症Ⅰ型合并胆囊癌,患者女性,61 岁,因“右上腹隐痛不适 2 月”入院;CT 扫描见胆囊腺瘤样占位(红色箭头);胆总管囊状扩张(黄色箭头);行胆囊癌根治性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及腹膜后淋巴结清扫、肝外胆管囊肿切除术,术后病理:胆囊腺癌,中分化;胆总管囊肿。F、g:示胆囊腺瘤癌变,其增强 CT 扫描(f)见胆囊壁腺瘤样结节占位强化病灶(红色箭头);行胆囊及临近胆囊床肝组织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骨骼化清扫及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术毕照片(g)。 h、i: 示胆囊底部恶性肿瘤,增强 CT 扫描(h)见胆囊底部囊壁显著增厚,局部强化;行胆囊及肝ⅣA 段和Ⅴ段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骨骼化清扫(12 组+8 组)、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13a 组),手术切除标本(i),其病理报告:胆囊腺癌,低分化,侵及胆囊床肝组织,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未见转移。j–l:示胆囊管癌侵犯肝门部胆管,MRCP(j)显示胆囊管汇入肝总管处截断阴影,远端胆管末端异常汇入胰管;行胆囊、肝门部及胆总管切除,临近胆囊床肝组织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骨骼化清扫(12 组+8 组)及腹膜后淋巴结清扫(13a 组)以及胆肠吻合术(k);手术标本剖检(l)
虽然目前胆囊癌的总体治疗有效率非常有限,但手术治疗仍是当下治疗胆囊癌最为积极而有效的手段[9-11]。肿瘤的根治性切除是胆囊癌手术治疗首要追求的目标,虽然随着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为肿瘤的治疗带来希望,但是胆囊癌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仍未获得突破性进展。因此,当下仍应强调尽可能实施完整的肿瘤切除,并力求切除组织的多切缘阴性。当术前影像学检查或术中探查发现肿瘤已发生肺、腹腔或肝内多发转移时,应放弃大范围腹腔肿瘤切除的努力;开展局部肿瘤切除再结合精准医学治疗应仅限于临床探索性研究。 因此,在胆囊癌的规范化手术治疗方面笔者认为主要涉及以下焦点问题。
1 胆囊癌的根治性切除范围
胆囊癌原发肿瘤部位可起源自胆囊底部、体部、颈部或胆囊管,不同部位肿瘤的根治性切除范围虽有所区别,但基本点是以原发肿瘤为中心、依照其侵犯或转移的病理生理特点进行手术范围规划,并对相应手术方案人群的总体预后进行研究、获得循证医学证据,以验证手术方案的合理性。总体而言,目前唯有 AJCC/UICC TNM 分期[1]能依据上述原则,对胆囊癌的手术治疗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1.1 肿瘤起源于胆囊底部、体部、颈部,未侵及肝门区域胆管的手术
AJCC/UICC TNM 分期第 8 版[12]在第 7 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肿瘤 T 分期作出的修改是针对 T2 期进行了细化分类,由第 7 版的“T2:肿瘤侵及肌肉周围结缔组织,尚未侵透浆膜或进入肝脏”进一步细分为第 8 版的“T2a:肿瘤侵入胆囊脏腹膜侧肌周结缔组织,尚未侵透浆膜; T2b,肿瘤侵入胆囊肝侧肌周结缔组织,尚未侵及肝脏”。此修改是基于对位于胆囊底部和体部的肝脏侧、非肝脏侧的 T2 期肿瘤作出了区分。研究[13]发现,胆囊床的囊壁缺少与肝脏相邻的浆膜层,肌周结缔组织与肝结缔组织相连,起源于胆囊床的肿瘤易侵入肝脏并转移。一项针对国际多中心(4 所医疗中心,437 例)胆囊癌手术病例的临床病理特点及术后生存分析的研究[14]发现,252 例 T2 期(AJCC/UICC TNM 分期第 7 版)病例中,肝脏侧生长的肿瘤的血管侵犯率、神经侵犯率和淋巴结转移率均高于腹膜侧生长的肿瘤,肝脏侧生长 T2 期病例术后 3 年和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52.1% 和 42.6%,腹膜侧生长 T2 期病例术后 3 年和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73.7% 和 64.7%。 在依照上述分类原则对 T1 期和 T3 期病例进行的术后预后随访均未观察到差异。
虽然 AJCC/UICC TNM 分期第 8 版对 T2 期胆囊癌的分类,意味着针对 T2a、T2b 分别实施联合肝切除或非肝切除的手术治疗方案设计具有合理性[15-16],但需要明确的是,如果术前无法通过影像学检查明确肿瘤尚未侵透胆囊浆膜或侵入肝脏,即术前诊断已明确为 T2 期(事实上 T1、T2 甚至 T3 分期多需病理检查方可作出准确诊断),依据肿瘤整体切除的 en bloc 原则,笔者建议对 T2 期以上的胆囊癌根治性手术切除范围应常规包括胆囊、临近胆囊床肝组织(肝切缘距胆囊 2 cm 以上[17])及区域淋巴结[18-20],根据肿瘤肝侵犯范围可相应扩大肝切除范围以求实现 R0 切除(图 1f-1i)。
1.2 肿瘤起源于胆囊颈部或胆囊管并侵犯肝门部区域胆管的手术
肿瘤起源于胆囊颈部或胆囊管易侵犯右肝管、左右肝管汇合部或肝总管等肝门部胆管区域,患者多合并有梗阻性黄疸。如果实施根治性切除,多需要联合肝门部胆管切除、扩大肝切除范围甚或联合右半肝切除。对此类情况采取手术治疗存在争议[21],争议的焦点在于患者手术需实施大范围肝切除方有可能获得 R0 切除机会,但因合并黄疸、肝储备功能显著下降,术后并发症高,且肿瘤恶性程度高、病情已处于进展期,预后总体不良,手术治疗是否还具有价值。笔者团队的临床实践[22]表明,如果能够实现肿瘤根治性切除,手术能够使患者获益(图 1j-1l),但术前需积极通过 PTCD 胆汁引流、胆汁回输等措施改善肝储备功能,制订“计划性肝切除”手术方案,并仔细评估术后可能增加的手术并发症风险等,审慎作出手术决策。
1.3 肿瘤侵犯至除肝门部胆管之外的其他器官的手术
当肿瘤或转移的淋巴结侵犯至胃、十二指肠、胰腺等胆囊周围脏器,虽然扩大切除范围有可能实现肿瘤 R0 切除(图 2a-2f),但鉴于胆囊癌高度恶性、辅助治疗效果不良、愈后极差的临床特点,扩大切除范围依然只是实现了肿瘤的局部治疗,并不能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却意味着患者需要承受更高的手术风险及术后并发症风险。因此应在综合考量患者年龄、身体状况、合并其他疾病、患者意愿、后续辅助治疗方案等情况下酌情实施[19]。
 图2
示胆囊癌实施“肝、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手术照片及胆囊结石伴胆囊癌变和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广泛转移的影像学检查结果
图2
示胆囊癌实施“肝、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手术照片及胆囊结石伴胆囊癌变和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广泛转移的影像学检查结果
a:手术探查见胆囊底部、体部质硬肿瘤,肝Ⅴ段、Ⅵ段及Ⅳb 段多发转移灶,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胰头部后上方多发肿大质硬淋巴结;b:行肝十二指肠韧带骨骼化清扫探查,发现胰头后上方转移淋巴结已侵犯胰头部;c:离断肝Ⅴ段、Ⅵ段、Ⅳb 段;d: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e:完成肝Ⅴ段、Ⅵ段、Ⅳb 段切除联合胰十二指肠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及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f:示肝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标本,术后病理诊断:胆囊底部、体部腺癌,中低分化,侵犯神经,胆囊腔内 3 枚结石、直径 0.6~2.2 cm;肝多发转移灶镜下形态同胆囊肿瘤,脉管内见癌栓;第 12 组、8 组及 13a 组淋巴结转移;肝切缘、肝门部胆管切缘、胰腺切缘和胃肠切缘均阴性。g–j:示胆囊结石伴胆囊癌变伴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广泛转移的影像学检查结果,CT 扫描动脉期(g)示胆囊占位、界限不清、肝右动脉受肿瘤侵犯,肝十二指肠韧带多发肿大淋巴结(h);门静脉期示肝门区域门静脉受肿瘤侵犯(i);PET-CT 检查(j)显示胆囊底部及胆囊床肝组织 FDG 高代谢影
1.4 肿瘤侵犯肝门部区域门静脉的手术
源自胆囊颈部和胆囊管的进展期肿瘤易侵犯门静脉,合并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转移时门静脉受淋巴结侵犯的概率也较高。当肿瘤侵犯门静脉右干或左、右干分叉部时,仅少数患者可通过联合右半肝切除、门静脉受侵段切除及血管重建术获益,但手术范围及创伤相应增大。当肿瘤侵犯门静脉主干范围局限时,行门静脉主干受侵段切除、血管重建具有指征。但当左、右双侧门静脉支均被肿瘤侵犯或门静脉主干广泛的包绕或梗阻时,已无法行肿瘤根治性切除,应放弃手术治疗(图 2g-2j)[18]。
2 淋巴结清扫范围
胆囊癌极易发生腹腔淋巴结转移,但对于胆囊癌的淋巴结清扫的范围和价值仍存在争议。胆囊存在至肝脏、胰腺后方淋巴结、腹腔干淋巴结、肠系膜根部等多条淋巴循环通路[23],因此胆囊底部、体部及颈部不同部位起源的肿瘤其淋巴结转移途径可能不同。笔者建议,根据日本 JSBS 分期[24],可将胆囊癌的淋巴结转移分为 3 站:N1、N2 和 N3。 N1 站限于肝十二指肠韧带内淋巴结,包括胆囊旁 12c 组、肝门横沟 12h 组、胆管旁 12b 组、门静脉后 12p 组及肝固有动脉旁 12a 组;胰腺后上第 13a 组和沿肝总动脉旁第 8 组为 N2 站转移;腹主动脉旁第 16 组、腹腔干旁第 9 组、肠系膜上动脉旁第 14 组或胰前第 17 组和胰腺后下第 13b 组淋巴结可视为 N3 站。近年来,笔者团队实施区域淋巴结清扫范围常规包括及限于 N1 站和 N2 站淋巴结。
胆囊癌肿瘤局部进展或淋巴结阳性提示已与不良预后相关[25],因此,当已确认合并有区域淋巴结转移,希冀扩大淋巴清扫范围以求改善预后的循证医学证据并不充分。笔者团队认为,当已明确发生区域淋巴结范围以外的淋巴结转移时,即使扩大淋巴结清扫范围也已不应视为肿瘤“根治性切除” ,不应常规实施。有文献[25]报道,部分患者术前实施新辅助化疗后再次进行手术可能会预后获益。
3 腹腔热灌注化疗胆囊癌手术治疗中的价值
腹腔热灌注化疗能够改善肿瘤侵犯至浆膜面和脏腹膜的结直肠癌[26]、空回肠腺癌腹膜转移[27]、恶性腹膜间皮瘤[28-29]等腹腔恶性肿瘤患者及多种肿瘤腹膜复发转移[30]患者的预后。 腹腔热灌注化疗在包括进展期胆囊癌的胆道恶性肿瘤中的治疗价值也已有报道[31-32]。笔者团队自 2015 年始,针对 T3–T4 期、肿瘤已侵犯至腹腔内脏器浆膜面病例,或胆囊癌术后复发、腹膜转移病例,开展肿瘤切除联合腹腔转移灶热灌注化疗的临床实践。 我们的阶段性工作总结(待发表)发现,联合腹腔转移灶热灌注化疗对控制肿瘤、消灭肿瘤腹腔内转移灶及恶性腹水具有效果、使患者预后获益(图 3a–3f)。因此笔者团队认为,联合腹腔转移灶热灌注化疗能使部分进展期胆囊癌患者获得手术治疗机会,对合并恶性腹水者具有改善其生活质量的治疗价值。
 图3
示进展期胆囊癌根治性切除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以及意外胆囊癌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 3 个月发现腹壁Trocar 窦道肿瘤种植转移情况
图3
示进展期胆囊癌根治性切除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以及意外胆囊癌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 3 个月发现腹壁Trocar 窦道肿瘤种植转移情况
a:CT 检查见胆囊实性占位病灶(红色箭头);b:术中见腹腔内恶性腹水;c:见胆囊肿瘤侵犯大网膜,肝脏恶性占位病灶已突破肝包膜;d:行肝ⅣB 段、Ⅴ段、Ⅵ段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及腹膜后淋巴结清扫,腹腔热灌注化疗;e:BR-TQR-Ⅱ型腹腔热灌注化疗系统操作、监控界面;f:术后四腔管法全腹腔热灌注化疗;g:见 Trocar 窦道、腹腔内及腹壁肿瘤种植转移;h:见Trocar 窦道及腹壁肿瘤种植转移
4 意外胆囊癌的再次手术
随着腹腔镜在临床的广泛开展,应重视“意外胆囊癌”的规范化诊疗。“意外胆囊癌”是指术前影像学诊断未提示胆囊癌、术中探查或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胆囊癌,术前肿瘤漏诊、误诊当排除在此概念范畴之外。
肿瘤位于底部或体部的意外胆囊癌,当病理诊断明确为 Tis 或 T1 期且术中未发生胆囊破溃者,可定期复查随访。Tis 及 T1 期术中发生胆囊破溃者,建议应在初次手术后 1~4 周内再次行临近胆囊床肝组织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术。既往多项临床研究[33-37]认为,病理诊断为 T1b 期(肿瘤已侵犯至胆囊肌层)单纯行胆囊切除术存在较高的肿瘤复发转移风险,多建议再次手术切除达到根治性切除和淋巴结清扫的范围。但 2018 年的一项国际多中心回顾性研究[38]发现,Ⅰ b 期胆囊癌分别实施单纯胆囊切除术(48.9%)和扩大范围的切除术(51.1%)后,2 组患者术后 5 年疾病相关生存期无显著差异,且 2 组间肿瘤位置和淋巴结转移对术后 5 年疾病相关生存期的影响也无差异。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对Ⅰ b 期胆囊癌再次手术治疗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但规范的根治性切除和淋巴结清扫范围能够提高转移淋巴结的阳性检出率,这对肿瘤 TNM 分期和辅助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意义[39]。笔者认为,意外胆囊癌的概念即表明,因术前和术中未建立胆囊癌的“临床诊断”,唯有通过术后病理诊断才能获得正确的诊断和分期,而病灶多点取材又对肿瘤的病理诊断和分期至关重要。因此,对患者作出“Ⅰ b 期意外胆囊癌”的诊断需极其谨慎。应详细了解病例首次手术切除标本的病理取材、诊断情况,必要时对胆囊标本再行病理切片、会诊。若无法确保病理分期限于Ⅰ b 期内,再手术具有临床现实意义。
肿瘤位于胆囊管的意外胆囊癌,再次手术治疗范围应进行更多考量。为求肿瘤阴性切缘,多需联合行肝外胆管切除、胆肠吻合术,或实施“胆囊管、胆总管汇合部的 T 形切除,胆管对端吻合术”,术中务必行胆管切缘快速病理检验以确保胆管近端及远端切缘均阴性[40]。此外,为防范初次手术可能导致肿瘤细胞接触 Trocar 窦道发生种植转移,再次手术时应联合窦道切除(图 3g、3h)[36]。
胆囊癌起源于胆囊底部、体部、颈部或胆囊管,是恶性程度极高的消化系统上皮性肿瘤。回顾胆囊癌包括手术、放疗、化疗、肿瘤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手段的进展,目前胆囊癌的预后仍令人失望。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国际抗癌联盟(AJCC/UICC)对美国 1989–1996 年诊断为胆囊癌的 10 705 例患者进行了随访 5 年以上的研究,证实随着肿瘤进展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人群 5 年生存率由 AJCC/UICC TNM 分期(第 7 版)[1]Ⅰ期的 50%,降至Ⅳa 期的 4%、Ⅳb 期的 2%[2]。因此,在胆囊癌仍缺乏有效的综合治疗的当下,对胆囊癌流行病学危险因素的有效管控,是防范其发生最为有效的措施。
胆囊结石是胆囊癌的首要风险因素(图 1a、1b)[3-6]。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作为一种特殊的胆囊慢性炎症,是胆囊的癌前病变(图 1c、1d)。此外,合并胆胰管汇合异常及胆管囊状扩张症会导致胆囊长期处于炎症状态,亦是胆囊癌的危险因素(图 1e)[7-8]。对上述胆囊癌癌前病变的危害性及其规范化治疗,应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
 图1
示不同情况胆囊癌手术切除标本或影像学照片
图1
示不同情况胆囊癌手术切除标本或影像学照片
a、b:示胆囊结石癌变病例手术切除标本,见胆囊结石、胆囊癌,肿瘤侵及胆囊床肝组织。c、d:示胆囊癌合并黄色肉芽肿,MRI(c)显示胆囊壁显著增厚,胆囊腔内实性占位病灶(红色星号),胆囊外壁尚光滑,胆囊周围肝组织未受肿瘤侵犯,胰头后方淋巴结肿大(黄色箭头);胆囊剖检(d):见胆囊底部及体部黄色肉芽肿(黑色星号),合并胆囊颈部腺癌(白色星号),肿瘤于胆囊腔内生长,未突破胆囊浆膜层。e:示先天性胆管囊状扩张症Ⅰ型合并胆囊癌,患者女性,61 岁,因“右上腹隐痛不适 2 月”入院;CT 扫描见胆囊腺瘤样占位(红色箭头);胆总管囊状扩张(黄色箭头);行胆囊癌根治性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及腹膜后淋巴结清扫、肝外胆管囊肿切除术,术后病理:胆囊腺癌,中分化;胆总管囊肿。F、g:示胆囊腺瘤癌变,其增强 CT 扫描(f)见胆囊壁腺瘤样结节占位强化病灶(红色箭头);行胆囊及临近胆囊床肝组织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骨骼化清扫及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术毕照片(g)。 h、i: 示胆囊底部恶性肿瘤,增强 CT 扫描(h)见胆囊底部囊壁显著增厚,局部强化;行胆囊及肝ⅣA 段和Ⅴ段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骨骼化清扫(12 组+8 组)、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13a 组),手术切除标本(i),其病理报告:胆囊腺癌,低分化,侵及胆囊床肝组织,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未见转移。j–l:示胆囊管癌侵犯肝门部胆管,MRCP(j)显示胆囊管汇入肝总管处截断阴影,远端胆管末端异常汇入胰管;行胆囊、肝门部及胆总管切除,临近胆囊床肝组织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骨骼化清扫(12 组+8 组)及腹膜后淋巴结清扫(13a 组)以及胆肠吻合术(k);手术标本剖检(l)
虽然目前胆囊癌的总体治疗有效率非常有限,但手术治疗仍是当下治疗胆囊癌最为积极而有效的手段[9-11]。肿瘤的根治性切除是胆囊癌手术治疗首要追求的目标,虽然随着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为肿瘤的治疗带来希望,但是胆囊癌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仍未获得突破性进展。因此,当下仍应强调尽可能实施完整的肿瘤切除,并力求切除组织的多切缘阴性。当术前影像学检查或术中探查发现肿瘤已发生肺、腹腔或肝内多发转移时,应放弃大范围腹腔肿瘤切除的努力;开展局部肿瘤切除再结合精准医学治疗应仅限于临床探索性研究。 因此,在胆囊癌的规范化手术治疗方面笔者认为主要涉及以下焦点问题。
1 胆囊癌的根治性切除范围
胆囊癌原发肿瘤部位可起源自胆囊底部、体部、颈部或胆囊管,不同部位肿瘤的根治性切除范围虽有所区别,但基本点是以原发肿瘤为中心、依照其侵犯或转移的病理生理特点进行手术范围规划,并对相应手术方案人群的总体预后进行研究、获得循证医学证据,以验证手术方案的合理性。总体而言,目前唯有 AJCC/UICC TNM 分期[1]能依据上述原则,对胆囊癌的手术治疗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1.1 肿瘤起源于胆囊底部、体部、颈部,未侵及肝门区域胆管的手术
AJCC/UICC TNM 分期第 8 版[12]在第 7 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肿瘤 T 分期作出的修改是针对 T2 期进行了细化分类,由第 7 版的“T2:肿瘤侵及肌肉周围结缔组织,尚未侵透浆膜或进入肝脏”进一步细分为第 8 版的“T2a:肿瘤侵入胆囊脏腹膜侧肌周结缔组织,尚未侵透浆膜; T2b,肿瘤侵入胆囊肝侧肌周结缔组织,尚未侵及肝脏”。此修改是基于对位于胆囊底部和体部的肝脏侧、非肝脏侧的 T2 期肿瘤作出了区分。研究[13]发现,胆囊床的囊壁缺少与肝脏相邻的浆膜层,肌周结缔组织与肝结缔组织相连,起源于胆囊床的肿瘤易侵入肝脏并转移。一项针对国际多中心(4 所医疗中心,437 例)胆囊癌手术病例的临床病理特点及术后生存分析的研究[14]发现,252 例 T2 期(AJCC/UICC TNM 分期第 7 版)病例中,肝脏侧生长的肿瘤的血管侵犯率、神经侵犯率和淋巴结转移率均高于腹膜侧生长的肿瘤,肝脏侧生长 T2 期病例术后 3 年和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52.1% 和 42.6%,腹膜侧生长 T2 期病例术后 3 年和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73.7% 和 64.7%。 在依照上述分类原则对 T1 期和 T3 期病例进行的术后预后随访均未观察到差异。
虽然 AJCC/UICC TNM 分期第 8 版对 T2 期胆囊癌的分类,意味着针对 T2a、T2b 分别实施联合肝切除或非肝切除的手术治疗方案设计具有合理性[15-16],但需要明确的是,如果术前无法通过影像学检查明确肿瘤尚未侵透胆囊浆膜或侵入肝脏,即术前诊断已明确为 T2 期(事实上 T1、T2 甚至 T3 分期多需病理检查方可作出准确诊断),依据肿瘤整体切除的 en bloc 原则,笔者建议对 T2 期以上的胆囊癌根治性手术切除范围应常规包括胆囊、临近胆囊床肝组织(肝切缘距胆囊 2 cm 以上[17])及区域淋巴结[18-20],根据肿瘤肝侵犯范围可相应扩大肝切除范围以求实现 R0 切除(图 1f-1i)。
1.2 肿瘤起源于胆囊颈部或胆囊管并侵犯肝门部区域胆管的手术
肿瘤起源于胆囊颈部或胆囊管易侵犯右肝管、左右肝管汇合部或肝总管等肝门部胆管区域,患者多合并有梗阻性黄疸。如果实施根治性切除,多需要联合肝门部胆管切除、扩大肝切除范围甚或联合右半肝切除。对此类情况采取手术治疗存在争议[21],争议的焦点在于患者手术需实施大范围肝切除方有可能获得 R0 切除机会,但因合并黄疸、肝储备功能显著下降,术后并发症高,且肿瘤恶性程度高、病情已处于进展期,预后总体不良,手术治疗是否还具有价值。笔者团队的临床实践[22]表明,如果能够实现肿瘤根治性切除,手术能够使患者获益(图 1j-1l),但术前需积极通过 PTCD 胆汁引流、胆汁回输等措施改善肝储备功能,制订“计划性肝切除”手术方案,并仔细评估术后可能增加的手术并发症风险等,审慎作出手术决策。
1.3 肿瘤侵犯至除肝门部胆管之外的其他器官的手术
当肿瘤或转移的淋巴结侵犯至胃、十二指肠、胰腺等胆囊周围脏器,虽然扩大切除范围有可能实现肿瘤 R0 切除(图 2a-2f),但鉴于胆囊癌高度恶性、辅助治疗效果不良、愈后极差的临床特点,扩大切除范围依然只是实现了肿瘤的局部治疗,并不能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却意味着患者需要承受更高的手术风险及术后并发症风险。因此应在综合考量患者年龄、身体状况、合并其他疾病、患者意愿、后续辅助治疗方案等情况下酌情实施[19]。
 图2
示胆囊癌实施“肝、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手术照片及胆囊结石伴胆囊癌变和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广泛转移的影像学检查结果
图2
示胆囊癌实施“肝、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手术照片及胆囊结石伴胆囊癌变和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广泛转移的影像学检查结果
a:手术探查见胆囊底部、体部质硬肿瘤,肝Ⅴ段、Ⅵ段及Ⅳb 段多发转移灶,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胰头部后上方多发肿大质硬淋巴结;b:行肝十二指肠韧带骨骼化清扫探查,发现胰头后上方转移淋巴结已侵犯胰头部;c:离断肝Ⅴ段、Ⅵ段、Ⅳb 段;d: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e:完成肝Ⅴ段、Ⅵ段、Ⅳb 段切除联合胰十二指肠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及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f:示肝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标本,术后病理诊断:胆囊底部、体部腺癌,中低分化,侵犯神经,胆囊腔内 3 枚结石、直径 0.6~2.2 cm;肝多发转移灶镜下形态同胆囊肿瘤,脉管内见癌栓;第 12 组、8 组及 13a 组淋巴结转移;肝切缘、肝门部胆管切缘、胰腺切缘和胃肠切缘均阴性。g–j:示胆囊结石伴胆囊癌变伴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广泛转移的影像学检查结果,CT 扫描动脉期(g)示胆囊占位、界限不清、肝右动脉受肿瘤侵犯,肝十二指肠韧带多发肿大淋巴结(h);门静脉期示肝门区域门静脉受肿瘤侵犯(i);PET-CT 检查(j)显示胆囊底部及胆囊床肝组织 FDG 高代谢影
1.4 肿瘤侵犯肝门部区域门静脉的手术
源自胆囊颈部和胆囊管的进展期肿瘤易侵犯门静脉,合并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转移时门静脉受淋巴结侵犯的概率也较高。当肿瘤侵犯门静脉右干或左、右干分叉部时,仅少数患者可通过联合右半肝切除、门静脉受侵段切除及血管重建术获益,但手术范围及创伤相应增大。当肿瘤侵犯门静脉主干范围局限时,行门静脉主干受侵段切除、血管重建具有指征。但当左、右双侧门静脉支均被肿瘤侵犯或门静脉主干广泛的包绕或梗阻时,已无法行肿瘤根治性切除,应放弃手术治疗(图 2g-2j)[18]。
2 淋巴结清扫范围
胆囊癌极易发生腹腔淋巴结转移,但对于胆囊癌的淋巴结清扫的范围和价值仍存在争议。胆囊存在至肝脏、胰腺后方淋巴结、腹腔干淋巴结、肠系膜根部等多条淋巴循环通路[23],因此胆囊底部、体部及颈部不同部位起源的肿瘤其淋巴结转移途径可能不同。笔者建议,根据日本 JSBS 分期[24],可将胆囊癌的淋巴结转移分为 3 站:N1、N2 和 N3。 N1 站限于肝十二指肠韧带内淋巴结,包括胆囊旁 12c 组、肝门横沟 12h 组、胆管旁 12b 组、门静脉后 12p 组及肝固有动脉旁 12a 组;胰腺后上第 13a 组和沿肝总动脉旁第 8 组为 N2 站转移;腹主动脉旁第 16 组、腹腔干旁第 9 组、肠系膜上动脉旁第 14 组或胰前第 17 组和胰腺后下第 13b 组淋巴结可视为 N3 站。近年来,笔者团队实施区域淋巴结清扫范围常规包括及限于 N1 站和 N2 站淋巴结。
胆囊癌肿瘤局部进展或淋巴结阳性提示已与不良预后相关[25],因此,当已确认合并有区域淋巴结转移,希冀扩大淋巴清扫范围以求改善预后的循证医学证据并不充分。笔者团队认为,当已明确发生区域淋巴结范围以外的淋巴结转移时,即使扩大淋巴结清扫范围也已不应视为肿瘤“根治性切除” ,不应常规实施。有文献[25]报道,部分患者术前实施新辅助化疗后再次进行手术可能会预后获益。
3 腹腔热灌注化疗胆囊癌手术治疗中的价值
腹腔热灌注化疗能够改善肿瘤侵犯至浆膜面和脏腹膜的结直肠癌[26]、空回肠腺癌腹膜转移[27]、恶性腹膜间皮瘤[28-29]等腹腔恶性肿瘤患者及多种肿瘤腹膜复发转移[30]患者的预后。 腹腔热灌注化疗在包括进展期胆囊癌的胆道恶性肿瘤中的治疗价值也已有报道[31-32]。笔者团队自 2015 年始,针对 T3–T4 期、肿瘤已侵犯至腹腔内脏器浆膜面病例,或胆囊癌术后复发、腹膜转移病例,开展肿瘤切除联合腹腔转移灶热灌注化疗的临床实践。 我们的阶段性工作总结(待发表)发现,联合腹腔转移灶热灌注化疗对控制肿瘤、消灭肿瘤腹腔内转移灶及恶性腹水具有效果、使患者预后获益(图 3a–3f)。因此笔者团队认为,联合腹腔转移灶热灌注化疗能使部分进展期胆囊癌患者获得手术治疗机会,对合并恶性腹水者具有改善其生活质量的治疗价值。
 图3
示进展期胆囊癌根治性切除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以及意外胆囊癌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 3 个月发现腹壁Trocar 窦道肿瘤种植转移情况
图3
示进展期胆囊癌根治性切除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以及意外胆囊癌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 3 个月发现腹壁Trocar 窦道肿瘤种植转移情况
a:CT 检查见胆囊实性占位病灶(红色箭头);b:术中见腹腔内恶性腹水;c:见胆囊肿瘤侵犯大网膜,肝脏恶性占位病灶已突破肝包膜;d:行肝ⅣB 段、Ⅴ段、Ⅵ段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及腹膜后淋巴结清扫,腹腔热灌注化疗;e:BR-TQR-Ⅱ型腹腔热灌注化疗系统操作、监控界面;f:术后四腔管法全腹腔热灌注化疗;g:见 Trocar 窦道、腹腔内及腹壁肿瘤种植转移;h:见Trocar 窦道及腹壁肿瘤种植转移
4 意外胆囊癌的再次手术
随着腹腔镜在临床的广泛开展,应重视“意外胆囊癌”的规范化诊疗。“意外胆囊癌”是指术前影像学诊断未提示胆囊癌、术中探查或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胆囊癌,术前肿瘤漏诊、误诊当排除在此概念范畴之外。
肿瘤位于底部或体部的意外胆囊癌,当病理诊断明确为 Tis 或 T1 期且术中未发生胆囊破溃者,可定期复查随访。Tis 及 T1 期术中发生胆囊破溃者,建议应在初次手术后 1~4 周内再次行临近胆囊床肝组织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术。既往多项临床研究[33-37]认为,病理诊断为 T1b 期(肿瘤已侵犯至胆囊肌层)单纯行胆囊切除术存在较高的肿瘤复发转移风险,多建议再次手术切除达到根治性切除和淋巴结清扫的范围。但 2018 年的一项国际多中心回顾性研究[38]发现,Ⅰ b 期胆囊癌分别实施单纯胆囊切除术(48.9%)和扩大范围的切除术(51.1%)后,2 组患者术后 5 年疾病相关生存期无显著差异,且 2 组间肿瘤位置和淋巴结转移对术后 5 年疾病相关生存期的影响也无差异。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对Ⅰ b 期胆囊癌再次手术治疗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但规范的根治性切除和淋巴结清扫范围能够提高转移淋巴结的阳性检出率,这对肿瘤 TNM 分期和辅助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意义[39]。笔者认为,意外胆囊癌的概念即表明,因术前和术中未建立胆囊癌的“临床诊断”,唯有通过术后病理诊断才能获得正确的诊断和分期,而病灶多点取材又对肿瘤的病理诊断和分期至关重要。因此,对患者作出“Ⅰ b 期意外胆囊癌”的诊断需极其谨慎。应详细了解病例首次手术切除标本的病理取材、诊断情况,必要时对胆囊标本再行病理切片、会诊。若无法确保病理分期限于Ⅰ b 期内,再手术具有临床现实意义。
肿瘤位于胆囊管的意外胆囊癌,再次手术治疗范围应进行更多考量。为求肿瘤阴性切缘,多需联合行肝外胆管切除、胆肠吻合术,或实施“胆囊管、胆总管汇合部的 T 形切除,胆管对端吻合术”,术中务必行胆管切缘快速病理检验以确保胆管近端及远端切缘均阴性[40]。此外,为防范初次手术可能导致肿瘤细胞接触 Trocar 窦道发生种植转移,再次手术时应联合窦道切除(图 3g、3h)[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