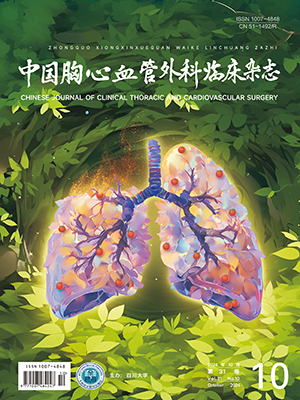引用本文: 徐波, 刘吉福, 戈明媚, 谭健, 吴冰, 叶金铎, 马静波, 张春秋. 漏斗胸术前心脏磁共振成像评估心脏结构和功能的临床价值.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15, 22(9): 862-865. doi: 10.7507/1007-4848.20150215 复制
漏斗胸畸形对人体生理的最大影响是压迫心脏和肺脏,以往采用的评价主要重视其对左心系统的影响,但并未获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近几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漏斗胸对心脏的影响主要是右心系统[1-2]。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4年6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行漏斗胸矫治术的患者54例,患者术前均做心脏核磁共振成像(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CMR)检查,评估其心脏形态和功能的变化。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54例漏斗胸患者诊断明确,无心脏病史,超声心动图检查示心脏无畸形,胸部CT检查显示凹陷的胸骨对心脏有压迫,而且需要手术治疗。男48例、女6例,年龄7~33岁(19.08±5.17)岁。根据年龄将患者分为儿童组和成人组。儿童组24例,年龄7~17(14.1±3.2)岁;漏斗胸分型Ⅰ型15例,Ⅱ型9例;胸廓指数(Haller index,HI) 3.2~5.8 (4.07±0.79);18例术前有胸闷气促,偶有胸痛、活动耐力低等症状,症状出现率为75.0% (18/24)。成人组30例,年龄18~33 (21.5±6.6) 岁;Ⅰ型19例,Ⅱ型8例;HI为3.2~25.8 (6.58±6.09);25例术前有胸闷、心悸、气促、活动耐力低等症状,症状出现率83.3% (25/30)。
1.2 方法
1.2.1 术前心脏结构和功能评价
采用CMR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CMR检查采用GE 1.5T超导型MR扫描仪。采用Report Card软件分析心脏结构和心室功能,在四腔心平面确定心室收缩期末和舒张期末图像后,测量右心室的长径和短径,并计算右心室长径和短径分别与体表面积的比值(即右心室长径指数和短径指数);记录右心室舒张期末容积(righ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RVEDV)和右心室收缩期末容积(righ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volume,RVESV)、右心室每博量(right ventricular stroke volume,RVSV),并计算右心室射血分数(righ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RVEF)。
1.2.2 心脏受压移位程度评价[1 ]
术前行胸部X线正侧位片,胸部CT扫描和三维重建,记录心脏受压类型和心脏移位程度,并做心电图。在CT电脑工作站测量,以胸骨与剑突交界水平测量心脏横径(A)和胸骨正中线左侧心脏横径(B),计算B/A值。据临床进行了修订,仍分为4度,正常:心脏在正中线左侧<60%;轻度移位:60%~70%;中度移位:71%~89%;重度移位:≥90%。
1.3 统计学分析
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2 结果
2.1 术前、后症状和HI的变化
5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胸壁畸形微创矫治。成人组术前症状出现率略高于儿童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3.3% (25/30) vs. 75.0% (18/24),P>0.05]。患者术后原有症状完全消失。儿童组术前、术后H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07±0.79 vs. 2.87±0.33,P<0.05),手术前后平均差值为1.24±0.64。成人组术前、术后HI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6.58±6.09 vs. 2.86±0.44,P<0.05),术前术后HI平均差值为3.67±0.79。
2.2 右心室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2.2.1 右心室结构的变化
胸骨及相应的肋软骨向胸内凹陷,对心脏的右心室压迫或压迫并推移,右心房或右室瓣环下局部受压凹陷,使右心室长径延长,短径变短畸变(图 1)。儿童组右心室长径45~110 (74.9±17.2) mm,短径9~31 (23.0±6.7) mm;成人组右心室长径62~106 (88.2±10.7) mm,短径12~51 (27.5±0.82) mm。成人组右心室长径和短径均显著大于儿童组(P<0.05)。儿童组右心室长、短径指数分别为60.39~61.73 (61.14±0.44) mm/m2、12.96~17.53(14.82±2.52) mm/m2;成人组右心室长、短径指数分别为48.37~63.1 (49.54±15.40) mm/m2、13.48~ 22.62(18.90±3.14) mm/m2 (表 1)。
 图1
男性,28岁。CMR示右心室严重压迫,右心呈畸变,右心室长径显著延长,短径缩短(直箭头示右心室受压重的部位,弯箭头示左心室)
图1
男性,28岁。CMR示右心室严重压迫,右心呈畸变,右心室长径显著延长,短径缩短(直箭头示右心室受压重的部位,弯箭头示左心室)
2.2.2 右心室功能的变化
儿童组RVEDV为45.1~183.7(121.50±31.27) ml;成人组为107.1~243.3 (139.09±29.08) ml;儿童组RVESV为26.3~111.1 (64.92±19.28) ml,成人组为44.6~120.4 (73.61±16.05) ml;儿童组RVEF为39%~53% (45.29%±4.14%),成人组为30%~60% (46.30%±6.09%)。成人组右心室RVEDV、RVESV均显著大于儿童组(P<0.05),但RVEF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2)。
2.3 心脏受压移位及与RVEF的相关性
儿童组发生心脏受压移位20例(83.3%),无移位4例(16.7%);其中轻度15例(62.5%),中度4例(16.7%),重度1例(4.1%)。成人组心脏受压移位27例(90.0%),无移位3例(10.0%);其中轻度13例(43.3%),中度9例(30.0%),重度5例(16.7%) (图 2)。成人组心脏中、重度移位发生率显著高于儿童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6.7% vs. 20.8%,P<0.05)。成人组心脏受压移位程度大于儿童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6.86%±13.30% vs. 67.99%±8.15%,P<0.05)。心脏移位程度与RVEF无显著相关性(r=0.12,P>0.05)。左心室结构功能均在正常范围之内。
 图2
女性,26岁。胸部CT轴位扫描示心脏受压向左侧推移至胸骨正中线左侧
图2
女性,26岁。胸部CT轴位扫描示心脏受压向左侧推移至胸骨正中线左侧
3 讨论
漏斗胸凹陷的胸骨及相连肋软骨产生对心脏的压迫早已被临床发现,长期以来大家仅注意观察心脏受压所致的形态变化,21世纪初逐渐开始探讨心脏受压对心功能的影响,主要是左心功能的影响,但获得的结果是阴性的,而患者有关心脏方面的症状从左心功能的状态来看又难以解释。最近几年,大家逐渐认识到右心功能受影响的重要性,并部分获得有阳性意义的结果。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极少,本研究可完善、充实漏斗胸对心脏影响的临床基础。
漏斗胸压迫致心脏畸变患者于术前采用CMR评估心脏结构和功能是一种可靠的方法。以往多采用M型或二维超声心动图、放射性照相测算法、核素心功能测定等,这些方法多不能获得临床需求的数据,而失去了应用价值。2008年Guntheroth等[3]据报道的漏斗胸术前后心功能研究进行荟萃分析,文献中仅有5篇符合要求,而且主要关注左心室的结构和功能,结果不能反映临床情况。随着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和软件功能发展,CMR已能对心脏解剖结构和功能进行评价,尤其是对先天性心脏病的评价;但是CMR用于漏斗胸右心功能评价还很少。
本组漏斗胸患者于术前行CMR检查,旨在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结果显示右心室的形态发生显著畸变,儿童组右心室长径、短径为(74.9±17.2) mm 和(23.0±6.7) mm,成人组的右心室长径、短径为(88.2±10.7) mm和(27.5±0.82) mm,与报道的正常人的右心室长径(69.3±9.7) mm和短径(30.6±6.6) mm 相比,最长径显著延长,短径缩短。为了避免右心室长、短径个体间的偏差,以右心室长径和短径分别与体表面积的比值计算右心室长、短径指数,儿童组右心室长、短径指数分别为(61.14±0.44) mm/m2和(14.82±2.52) mm/m2,成人组右心室长、短径指数分别为(49.54±15.40) mm/m2和(18.90±3.14) mm/m2,与正常成年人右心室长、短径指数(39.4±5.5) mm/m2和(18.1±3.4) mm/m2相比显著增大,说明漏斗胸患者右心室长、短径均大于正常人。本研究中儿童右心室长径指数大于成人,可能说明漏斗胸胸骨向内凹陷对右心室的压迫并非随着年龄增长而右心室长径延长,即右心室的延长是有限度的。
另外,本组漏斗胸患者右心室的功能也有明显变化。儿童组RVESV为64.92 ml,成人组为73.61 ml,较正常成人RVESV 45.6 ml显著增高。儿童组和成人组患者RVEF为45.29%±4.14%和46.30%±6.09%,与正常人RVEF 58.2%±7.4%相比显著降低[4],这些均说明右心室功能受到了损害。Saleh等[5]曾对30例漏斗胸患者与25例正常人进行对照研究,静态下用CMR评价右心功能,其结果与本研究一致。从研究结果看,漏斗胸患者右心室功能明显异常,尽管还未导致心功能障碍,但也足以说明漏斗胸有心脏受压出现,应积极进行手术矫治。
关于漏斗胸矫治的疗效评估,以往文献主要是从外观和影像学对胸廓外形进行评价,对心功能状况进行术后评估很少见[1, 6]。本组术前有症状的患者术后相关症状消失,尽管术后因患者体内置入矫形板而不能行CMR检查,但也间接说明矫形治疗的有效性。在Humphries等[7]研究发现漏斗胸矫治术后心脏受压情况改善的基础上,Maagaard等[8]研究对有症状漏斗胸采用胸骨翻转矫治,术前、后均行CMR检查,发现术后83%的患者右心房、右心室压迫完全解除。亦有研究采用运动状态用超声心动图和肺功能评价漏斗胸术前、后心脏指数和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运动状态更能反映漏斗胸患者的心功能状态[9]。
临床上大部分漏斗胸患者有劳力性呼吸困难,易疲劳,偶有胸痛。本研究中成人组症状发生率高达83.3%,高于儿童组,但漏斗胸致心脏移位程度与右心功能RVEF指标无显著相关性,这可能与漏斗胸对心脏的压迫方式有关,有报道其临床体征出现奇脉与下腔静脉压迫有关[2],也有报道其症状的出现与心肺压迫或心理因素有关[9]。漏斗胸长期持久地压迫心脏是否对心肌造成损害,心脏受压是否影响心肌的收缩,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文献中尚未见报道。但有研究发现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心室长径与心肌收缩有关,Sehata等[10-11]采用CMR心肌标签技术,观察心肌收缩的滑动长度,结果显示当心室长径延长时,则心肌滑动收缩长度变短,从而影响心肌收缩。漏斗胸压迫心脏的最大变化是右心室长径显著增大,对心肌造成的潜在或直接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总之,用CMR检查术前评价受漏斗胸压迫的心脏结构和功能是一种可靠的方法,可以为漏斗胸对心脏的损害提供依据,一旦出现心脏受压即为漏斗胸矫治的强烈指征。
漏斗胸畸形对人体生理的最大影响是压迫心脏和肺脏,以往采用的评价主要重视其对左心系统的影响,但并未获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近几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漏斗胸对心脏的影响主要是右心系统[1-2]。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4年6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行漏斗胸矫治术的患者54例,患者术前均做心脏核磁共振成像(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CMR)检查,评估其心脏形态和功能的变化。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54例漏斗胸患者诊断明确,无心脏病史,超声心动图检查示心脏无畸形,胸部CT检查显示凹陷的胸骨对心脏有压迫,而且需要手术治疗。男48例、女6例,年龄7~33岁(19.08±5.17)岁。根据年龄将患者分为儿童组和成人组。儿童组24例,年龄7~17(14.1±3.2)岁;漏斗胸分型Ⅰ型15例,Ⅱ型9例;胸廓指数(Haller index,HI) 3.2~5.8 (4.07±0.79);18例术前有胸闷气促,偶有胸痛、活动耐力低等症状,症状出现率为75.0% (18/24)。成人组30例,年龄18~33 (21.5±6.6) 岁;Ⅰ型19例,Ⅱ型8例;HI为3.2~25.8 (6.58±6.09);25例术前有胸闷、心悸、气促、活动耐力低等症状,症状出现率83.3% (25/30)。
1.2 方法
1.2.1 术前心脏结构和功能评价
采用CMR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CMR检查采用GE 1.5T超导型MR扫描仪。采用Report Card软件分析心脏结构和心室功能,在四腔心平面确定心室收缩期末和舒张期末图像后,测量右心室的长径和短径,并计算右心室长径和短径分别与体表面积的比值(即右心室长径指数和短径指数);记录右心室舒张期末容积(righ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RVEDV)和右心室收缩期末容积(righ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volume,RVESV)、右心室每博量(right ventricular stroke volume,RVSV),并计算右心室射血分数(righ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RVEF)。
1.2.2 心脏受压移位程度评价[1 ]
术前行胸部X线正侧位片,胸部CT扫描和三维重建,记录心脏受压类型和心脏移位程度,并做心电图。在CT电脑工作站测量,以胸骨与剑突交界水平测量心脏横径(A)和胸骨正中线左侧心脏横径(B),计算B/A值。据临床进行了修订,仍分为4度,正常:心脏在正中线左侧<60%;轻度移位:60%~70%;中度移位:71%~89%;重度移位:≥90%。
1.3 统计学分析
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2 结果
2.1 术前、后症状和HI的变化
5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胸壁畸形微创矫治。成人组术前症状出现率略高于儿童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3.3% (25/30) vs. 75.0% (18/24),P>0.05]。患者术后原有症状完全消失。儿童组术前、术后H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07±0.79 vs. 2.87±0.33,P<0.05),手术前后平均差值为1.24±0.64。成人组术前、术后HI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6.58±6.09 vs. 2.86±0.44,P<0.05),术前术后HI平均差值为3.67±0.79。
2.2 右心室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2.2.1 右心室结构的变化
胸骨及相应的肋软骨向胸内凹陷,对心脏的右心室压迫或压迫并推移,右心房或右室瓣环下局部受压凹陷,使右心室长径延长,短径变短畸变(图 1)。儿童组右心室长径45~110 (74.9±17.2) mm,短径9~31 (23.0±6.7) mm;成人组右心室长径62~106 (88.2±10.7) mm,短径12~51 (27.5±0.82) mm。成人组右心室长径和短径均显著大于儿童组(P<0.05)。儿童组右心室长、短径指数分别为60.39~61.73 (61.14±0.44) mm/m2、12.96~17.53(14.82±2.52) mm/m2;成人组右心室长、短径指数分别为48.37~63.1 (49.54±15.40) mm/m2、13.48~ 22.62(18.90±3.14) mm/m2 (表 1)。
 图1
男性,28岁。CMR示右心室严重压迫,右心呈畸变,右心室长径显著延长,短径缩短(直箭头示右心室受压重的部位,弯箭头示左心室)
图1
男性,28岁。CMR示右心室严重压迫,右心呈畸变,右心室长径显著延长,短径缩短(直箭头示右心室受压重的部位,弯箭头示左心室)
2.2.2 右心室功能的变化
儿童组RVEDV为45.1~183.7(121.50±31.27) ml;成人组为107.1~243.3 (139.09±29.08) ml;儿童组RVESV为26.3~111.1 (64.92±19.28) ml,成人组为44.6~120.4 (73.61±16.05) ml;儿童组RVEF为39%~53% (45.29%±4.14%),成人组为30%~60% (46.30%±6.09%)。成人组右心室RVEDV、RVESV均显著大于儿童组(P<0.05),但RVEF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2)。
2.3 心脏受压移位及与RVEF的相关性
儿童组发生心脏受压移位20例(83.3%),无移位4例(16.7%);其中轻度15例(62.5%),中度4例(16.7%),重度1例(4.1%)。成人组心脏受压移位27例(90.0%),无移位3例(10.0%);其中轻度13例(43.3%),中度9例(30.0%),重度5例(16.7%) (图 2)。成人组心脏中、重度移位发生率显著高于儿童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6.7% vs. 20.8%,P<0.05)。成人组心脏受压移位程度大于儿童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6.86%±13.30% vs. 67.99%±8.15%,P<0.05)。心脏移位程度与RVEF无显著相关性(r=0.12,P>0.05)。左心室结构功能均在正常范围之内。
 图2
女性,26岁。胸部CT轴位扫描示心脏受压向左侧推移至胸骨正中线左侧
图2
女性,26岁。胸部CT轴位扫描示心脏受压向左侧推移至胸骨正中线左侧
3 讨论
漏斗胸凹陷的胸骨及相连肋软骨产生对心脏的压迫早已被临床发现,长期以来大家仅注意观察心脏受压所致的形态变化,21世纪初逐渐开始探讨心脏受压对心功能的影响,主要是左心功能的影响,但获得的结果是阴性的,而患者有关心脏方面的症状从左心功能的状态来看又难以解释。最近几年,大家逐渐认识到右心功能受影响的重要性,并部分获得有阳性意义的结果。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极少,本研究可完善、充实漏斗胸对心脏影响的临床基础。
漏斗胸压迫致心脏畸变患者于术前采用CMR评估心脏结构和功能是一种可靠的方法。以往多采用M型或二维超声心动图、放射性照相测算法、核素心功能测定等,这些方法多不能获得临床需求的数据,而失去了应用价值。2008年Guntheroth等[3]据报道的漏斗胸术前后心功能研究进行荟萃分析,文献中仅有5篇符合要求,而且主要关注左心室的结构和功能,结果不能反映临床情况。随着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和软件功能发展,CMR已能对心脏解剖结构和功能进行评价,尤其是对先天性心脏病的评价;但是CMR用于漏斗胸右心功能评价还很少。
本组漏斗胸患者于术前行CMR检查,旨在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结果显示右心室的形态发生显著畸变,儿童组右心室长径、短径为(74.9±17.2) mm 和(23.0±6.7) mm,成人组的右心室长径、短径为(88.2±10.7) mm和(27.5±0.82) mm,与报道的正常人的右心室长径(69.3±9.7) mm和短径(30.6±6.6) mm 相比,最长径显著延长,短径缩短。为了避免右心室长、短径个体间的偏差,以右心室长径和短径分别与体表面积的比值计算右心室长、短径指数,儿童组右心室长、短径指数分别为(61.14±0.44) mm/m2和(14.82±2.52) mm/m2,成人组右心室长、短径指数分别为(49.54±15.40) mm/m2和(18.90±3.14) mm/m2,与正常成年人右心室长、短径指数(39.4±5.5) mm/m2和(18.1±3.4) mm/m2相比显著增大,说明漏斗胸患者右心室长、短径均大于正常人。本研究中儿童右心室长径指数大于成人,可能说明漏斗胸胸骨向内凹陷对右心室的压迫并非随着年龄增长而右心室长径延长,即右心室的延长是有限度的。
另外,本组漏斗胸患者右心室的功能也有明显变化。儿童组RVESV为64.92 ml,成人组为73.61 ml,较正常成人RVESV 45.6 ml显著增高。儿童组和成人组患者RVEF为45.29%±4.14%和46.30%±6.09%,与正常人RVEF 58.2%±7.4%相比显著降低[4],这些均说明右心室功能受到了损害。Saleh等[5]曾对30例漏斗胸患者与25例正常人进行对照研究,静态下用CMR评价右心功能,其结果与本研究一致。从研究结果看,漏斗胸患者右心室功能明显异常,尽管还未导致心功能障碍,但也足以说明漏斗胸有心脏受压出现,应积极进行手术矫治。
关于漏斗胸矫治的疗效评估,以往文献主要是从外观和影像学对胸廓外形进行评价,对心功能状况进行术后评估很少见[1, 6]。本组术前有症状的患者术后相关症状消失,尽管术后因患者体内置入矫形板而不能行CMR检查,但也间接说明矫形治疗的有效性。在Humphries等[7]研究发现漏斗胸矫治术后心脏受压情况改善的基础上,Maagaard等[8]研究对有症状漏斗胸采用胸骨翻转矫治,术前、后均行CMR检查,发现术后83%的患者右心房、右心室压迫完全解除。亦有研究采用运动状态用超声心动图和肺功能评价漏斗胸术前、后心脏指数和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运动状态更能反映漏斗胸患者的心功能状态[9]。
临床上大部分漏斗胸患者有劳力性呼吸困难,易疲劳,偶有胸痛。本研究中成人组症状发生率高达83.3%,高于儿童组,但漏斗胸致心脏移位程度与右心功能RVEF指标无显著相关性,这可能与漏斗胸对心脏的压迫方式有关,有报道其临床体征出现奇脉与下腔静脉压迫有关[2],也有报道其症状的出现与心肺压迫或心理因素有关[9]。漏斗胸长期持久地压迫心脏是否对心肌造成损害,心脏受压是否影响心肌的收缩,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文献中尚未见报道。但有研究发现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心室长径与心肌收缩有关,Sehata等[10-11]采用CMR心肌标签技术,观察心肌收缩的滑动长度,结果显示当心室长径延长时,则心肌滑动收缩长度变短,从而影响心肌收缩。漏斗胸压迫心脏的最大变化是右心室长径显著增大,对心肌造成的潜在或直接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总之,用CMR检查术前评价受漏斗胸压迫的心脏结构和功能是一种可靠的方法,可以为漏斗胸对心脏的损害提供依据,一旦出现心脏受压即为漏斗胸矫治的强烈指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