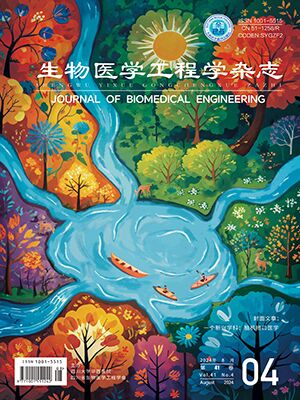作为典型的负性情绪,恐惧情绪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并显著影响人类行为。深入了解负性情绪的产生机制有助于提高相关疾病的诊疗效果。然而大脑面对恐惧情绪刺激时的神经机制依旧不明。为此,本研究在早期后部负波(EPN)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将脑电图(EEG)源分析和皮层脑网络构建相结合,从时-空角度探索了恐惧和中性情绪图片刺激下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差异。结果发现中性情绪刺激能够比恐惧刺激诱发更高幅值的EPN。进一步通过对包含EPN成分的EEG数据执行溯源分析发现,恐惧和中性情绪刺激下的大脑皮层激活区域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在alpha频段脑网络观察到恐惧情绪相比中性情绪存在更多的功能连接。通过量化脑网络属性发现,与中性情绪相比,恐惧情绪刺激下的平均节点度和平均聚类系数明显更大。结果表明,将ERP、EEG溯源以及脑网络分析相结合,有助于以较高的时-空分辨率探究恐惧情绪处理进程中的脑功能调制,也为探索负性情绪的神经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引用本文: 臧倩, 赵小茗, 梁铁, 刘秀玲, 娄存广. 情绪刺激下恐惧反应的神经机制:结合早期后部负波和脑电图源网络分析的初步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24, 41(5): 951-957. doi: 10.7507/1001-5515.202403052 复制
0 引言
情绪是一种主观的体验,通常表现为对某种刺激的情感反应,如高兴、悲伤、厌恶、恐惧等。情绪对我们的思维、行为和身体反应产生影响,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恐惧作为常见的负性情绪,尽管已在生物学意义、生理基础及认知功能等多个维度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广泛研究,但恐惧情绪加工的神经机制仍不明确[1-3]。深入了解恐惧情绪背后的神经机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情感体验的产生和调节过程,进而进一步诊断和治疗与负性情绪相关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等。
之前基于脑成像的相关研究表明,恐惧刺激能够激活左舌回、左侧杏仁核以及左侧前额叶皮层等区域[4-5]。另外一些研究发现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对主观恐惧的认知调节起关键作用[6-7]。这些研究为证实恐惧情绪与特定脑区的激活存在相关性提供了充分证据。然而情绪的产生是瞬时发生的事件,脑成像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在时间分辨率上的不足限制了在更精细的时间过程中探索情绪处理机制。
得益于非侵入式神经电生理采集技术的发展,高时间分辨率的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信号被广泛应用于开展情绪研究。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技术能够反映特定事件刺激引起的大脑活动进程,是目前基于EEG信号开展情绪研究的重要方法[8-9]。早期后部负波(early posterior negativity,EPN)是当前ERP情绪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成分,它通常出现于视觉刺激呈现后的100 ~ 350 ms内,且在头皮颞枕部区域最为明显[10]。EPN反映了大脑对于视觉刺激的早期处理,被认为是与注意力资源量相关的选择性情绪感知的最早处理的标志[11]。先前的研究已证实EPN成分普遍存在于恐惧情绪刺激的实验条件下,并证实了EPN可以被用于表征大脑对恐惧情绪的视觉刺激信息的处理进程[12-13]。然而情绪产生是一种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大脑多区域的激活与相互作用[14]。尽管当前基于EPN的研究揭示了恐惧情绪处理过程中时间锁定的同步神经活动,但大多数忽略了大脑各区域在此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近年,网络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研究者们可以从网络的角度去研究情绪相关的大脑活动[15]。利用EEG信号构建并深入研究对应的脑功能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深入理解情绪处理过程中大脑全局调控机制的新视角,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情绪处理的神经机制。然而,大部分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大脑视觉刺激的信息处理进程,导致无法准确构建情绪处理过程中时间锁定的脑功能网络。而且,大部分基于EEG的脑功能网络的情绪研究都是利用头皮EEG信号来构建,而EEG信号存在严重的体积传导效应,这直接导致了它较低的空间分辨率,进而易导致脑功能网络构建不准确[16]。EEG溯源技术已被证实可以在确保EEG信号高时间分辨率的基础上有效提升其空间分辨率,有助于构建更准确的脑网络[17]。
本研究通过不同场景的情绪图片诱发健康受试者的恐惧和中性情绪,同步记录64通道EEG信号。随后,采用ERP技术探索两种情绪EPN成分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sLORETA方法对EEG信号执行溯源分析,进而基于图论构建并分析不同情绪状态下的源层面脑功能网络。本研究将ERP、EEG溯源以及脑网络分析相结合,探索视觉刺激诱发的恐惧情绪和中性情绪时间锁定的脑皮层电活动以及相关的脑网络调节机制,以期为负性情绪机制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为情绪障碍患者的诊疗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临床实践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本研究成功招募了20名健康成年受试者,包括10名男性和10名女性,年龄为(22.7 ± 2.2)岁。所有受试者均为右利手,且未患有任何精神类疾病。此外,所有受试者的视力或矫正视力均符合实验要求。在正式实验开始前,所有受试者详细了解了实验流程和需注意的事项,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由于实验中存在恐惧刺激,提前告知受试者能否接受,并且剔除掉胆子非常小和经常看恐怖电影的受试者,防止出现极端的个体差异。
所选刺激材料均为图片,选自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18]。首先在负性图片中初步选取了一些可能诱发恐惧的图片,代表图片有鬼脸、蛇、尸体和血腥等场景。考虑到每个人对恐惧的感受不同,负性图片再由受试者通过九点评分量表进行筛选,选取出他们认为恐惧和中性的图片。最终确定了30张恐惧图片(效价为2.38 ± 0.46,唤醒度为5.78 ± 0.63)。为防止恐惧图片连续多次出现引起的信息加工异化,又选取了60张中性图片(效价为5.49 ± 0.37,唤醒度为3.74 ± 0.51)。对所选材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恐惧图片的唤醒度和效价明显高于中性图片(P < 0.001)。
采用E-Prime 2.0专业软件编制实验范式,图片呈现于电脑屏幕。所有图片随机出现,均只出现一次。每试次开始时,黑色屏幕中央出现红色注视点,持续1 000 ms,之后呈现图片。每张图片的展示时间为3 000 ms,期间要求受试者保持自然注视状态,以便充分体验图片所诱发的情感反应。图片消失后,受试者需进行按键操作用于判断图片类型,其中1代表恐惧,2代表其他类别。整个实验流程如图1所示。实验总计120个试次,每30个试次受试者被允许休息一次。为让受试者熟悉实验流程,在正式实验开始前进行一次简单的预实验。在预实验中,选用同样来自IAPS的刺激图片,其中包括中性图片和恐惧图片各10张。预实验的操作流程严格遵循正式实验的标准,确保实验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实验在安静、光线暗的屏蔽室内进行,确保受试者身心放松并避免过多动作。
 图1
实验范式
图1
实验范式
实验开始时,屏幕中央出现红色注视点,持续1 000 ms。之后随机呈现情绪刺激图片3 000 ms。受试者在图片消失后通过按键判断图片类型(1为恐惧,2为其他)。右侧图片为恐惧情绪图片示例
Figure1. Experimental paradigmat the start of the experiment, a red fixation point appeared at the center of the screen and lasted for 1 000 ms. Subsequently, emotional stimulus images were randomly presented for 3 000 ms.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judge the type of the image (1 for fear, 2 for other) by pressing a key after the image disappeared. The four pictures on the right are examples of fear pictures
1.2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本研究中采用脑电采集系统(Neuroscan,澳大利亚)按照国际10-20标准以500 Hz采样率采集64通道EEG信号。实验过程中确保电极阻抗小于5 kΩ。EEG数据离线预处理在EEGLAB执行。首先将采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带通滤波(0.1~ 40 Hz),并根据信号质量决定是否剔除坏道,使用独立成分分析方法去除常见伪迹(如眼电、心电和肌电)。随后将幅值超过±100 μV的数据段全部剔除,有效数据长度设定为–200 ~ 3 000 ms(刺激图片出现时刻标注为0 ms,–200 ms代表刺激图片出现前200 ms)。同时去除受试者判断错误的试次,预处理后保留80%的有效试次,确保每个受试者每种条件下可供ERP分析的试次不少于23次。最终获得62导的EEG信号用于后续分析。在进行ERP分析时选取双侧乳突M1、M2为参考,在进行脑功能分析时参考改为全脑平均参考。
1.3 数据分析
首先,–200 ~ 800 ms的EEG数据被截取用于执行ERP分析。以刺激图片出现为0 ms,基线为图片呈现前200 ms,执行基线校正后分别对两种不同情绪刺激下的ERP活动进行叠加平均并进行统计分析。
随后,对包含EPN(250 ~ 450 ms)成分的EEG信号的平均波幅进行溯源分析。采用sLORETA算法,通过对采集到的头皮电极信号执行逆运算,求得大脑皮层各个脑区的电流密度分布[19]。在假定大脑皮层激活模式一致的前提下,分布于大脑皮层的电流密度源信号通过线性叠加的方式,最终在头皮上得以记录(即EEG信号)。
本研究使用Brainstorm软件实现溯源分析,采用t检验方法来检验条件之间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为进一步确定不同情绪下EPN成分的脑区连通性,将溯源后的EEG数据执行功能连接分析。采用相干性方法计算任意两脑区间的耦合强度作为节点连接边。
相干性作为衡量信号在特定频率下线性耦合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刻画了不同信号间的关联程度。给定信号x和y,它们之间的相干性可以通过式(1)进行量化描述为:
 |
式中,Pxy(f)代表信号x和y之间的交叉功率谱密度,而Pxx(f)和Pyy(f)代表各自的功率谱密度。
将之前sLORETA源定位的结果依据Desikan–Killiany–Tourville(DKT)模版映射至68个脑区,每个脑区的平均源信号作为该脑区的代表信号。分别在theta(4 ~ 8 Hz)、alpha(8 ~ 13 Hz)、beta(13 ~ 30 Hz)以及gamma(30 ~ 35 Hz)四个频段内计算平均源信号之间的相干性。最终每个受试者得到每种情绪下68*68*4的相干性矩阵。
分别在不同频段内对所有受试者两种情绪状态的连接矩阵检验零假设,即该条边的强度在不同情绪之间没有变化,采用的t统计量为:
 |
式中, 和
和 分别是两种情绪矩阵连接边的均值,
分别是两种情绪矩阵连接边的均值, 和
和 分别是两种情绪矩阵连接边的方差。通过置换检验(N = 10 000)来估计t统计量的分布,然后与原始值进行比较来确定每条边是否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选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连接矩阵所在频段。
分别是两种情绪矩阵连接边的方差。通过置换检验(N = 10 000)来估计t统计量的分布,然后与原始值进行比较来确定每条边是否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选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连接矩阵所在频段。
鉴于全连接矩阵在网络属性计算时涉及庞大的计算量,有必要对全连接矩阵进行阈值化处理。在阈值的选择上,研究者们常常以Kcost作为参考量来设定阈值,具体方式如式(3)所示:
 |
式中,Ki表示节点度,而N代表网络中节点总数。当Kcost的值等于P,并且处于0.05 ~ 0.35之间时,网络所展现出的拓扑结构属性与大脑网络的特性相近。此外,为了维持脑网络的连通性,网络的平均节点度应当满足一定的条件,即ln(N)≤Knet≤N。这一范围确保了脑网络在结构上的连通性与稳定性。本研究中,BrainNet Viewer软件被用于对阈值化后的连接矩阵进行可视化。
利用每个特定频段的脑网络计算网络属性,具体包括节点度和节点聚类系数。节点度表示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个数,即:
 |
式中,N表示网络中节点的总数,hij则代表矩阵中的相邻元素。
节点聚类系数是用来衡量一个节点与其邻近节点之间形成连接关系的可能性,反映了该节点在网络中的局部连接特性,即
 |
式中,Wi为与节点i相连的ki个节点间的实际连接边数,Mi为ki个节点间可能存在的最大连接边数,Ei表示节点i的ki个邻节点之间实际存在的边数。平均聚类系数则是对所有节点的聚类系数求平均值,提供了对整个网络局部连接紧密程度的整体评估。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两种情绪状态下的脑网络平均节点度和平均聚类系数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检验水准为0.05)。
2 结果
对于EPN成分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与中性情绪相比,恐惧情绪诱发了更大的EPN波幅(P < 0.05)。两种情绪条件下的ERP总平均波形见图2。
 图2
不同情绪图片刺激下代表性电极位置EPN总平均波形图
图2
不同情绪图片刺激下代表性电极位置EPN总平均波形图
图中阴影标注区域为出现的EPN成分
Figure2. Grand average waveform of the representative electrode position of EPN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pictures stimulithe shaded area in the figure indicates the occurrence of EPN components
由图3可见,恐惧情绪图片刺激下EPN成分的激活区域主要在缘上回、顶叶下回、左侧额中回下部、左侧颞下回、右侧颞叶、距状旁回、右侧楔前叶、扣带回峡部、前扣带回后部和右侧舌回,并且右侧顶叶下回的电流密度高于左侧。中性情绪图片刺激下EPN成分的激活区域主要为右枕叶外侧、右侧顶叶下回、左侧额中回下部、右侧额下回、右侧距状旁回、颞极区、额上回和内侧眶额。相比于恐惧情绪,中性情绪图片刺激下左脑的激活区域明显变少。
 图3
不同情绪图片刺激下的溯源分析结果及对比
Figure3.
Source analysis results and comparisons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pictures stimuli
图3
不同情绪图片刺激下的溯源分析结果及对比
Figure3.
Source analysis results and comparisons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pictures stimuli
进而,分析了两种情绪下大脑皮层活动差异的脑区,结果如图3所示。恐惧情绪和中性情绪的EPN源差异主要在右外侧眶额、左侧额中回下部、右侧额下回、右侧顶叶、左侧缘上回、左侧颞下回、右侧颞上回、右侧颞中回和楔前叶。
本研究针对每个受试者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四个频带脑网络进行了置换检验,仅在alpha频段发现了恐惧情绪与中性情绪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alpha频段下各情绪状态阈值化后的脑皮层功能网络(选取的阈值为0.5)如图4所示,可以看到,中性情绪状态下脑网络中连接边数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额叶和一部分顶叶。相比之下,恐惧情绪状态下连接数量明显更多,主要集中在颞叶和顶叶,表明负性情绪对大脑功能连接有着显著的影响。
 图4
不同情绪状态下alpha频段阈值化连接矩阵及脑网络
Figure4.
Thresholding connectivity matrix and visual brain network of alpha band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states
图4
不同情绪状态下alpha频段阈值化连接矩阵及脑网络
Figure4.
Thresholding connectivity matrix and visual brain network of alpha band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states
表1展示了恐惧情绪和中性情绪下脑网络的平均节点度和平均聚类系数。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与中性情绪相比,恐惧情绪状态下的脑网络表现出更高的平均节点度和平均聚类系数,这一发现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情绪状态对脑网络结构的影响。
3 讨论及结论
本研究将ERP、EEG溯源分析和源层面脑功能网络相结合,探索了视觉刺激诱发的恐惧和中性情绪的脑皮层活动及大脑功能调制。
本研究首先探索了恐惧和中性情绪刺激下EPN成分的差异。结果发现,相较于中性情绪,恐惧情绪诱发出了更高的EPN幅值。EPN作为一种ERP的重要成分,振幅被证实与情绪唤醒度相关,也与图片的情绪内容相关[20]。本研究中与刺激强度相关的EPN幅值增大的结果可能反映了情绪加工过程中注意力资源的分配,即相较于中性刺激,恐惧刺激更能引起受试者的注意[12]。本研究中,利用恐惧图片刺激受试者,观察到更为显著的EPN,这表明恐惧刺激有效激活了情绪生成系统,引发了受试者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应。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不同情绪状态会导致不同的大脑激活模式的观点。
通过对包含EPN成分的250 ~ 450 ms平均波幅的溯源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恐惧情绪和中性情绪EPN的源差异主要出现在右外侧眶额、左侧额中回下部、右侧额下回、右侧顶叶、左侧缘上回、左侧颞下回、右侧颞上回、右侧颞中回和楔前叶等区域。之前有研究认为左侧缘上回和左侧杏仁核在恐惧情绪的产生和表达中起重要作用,在面对威胁性刺激时,缘上回和杏仁核的活动会增加,并且与恐惧体验的强度呈正相关[21]。还有研究发现,左侧前额叶皮层和扣带回皮层也参与了恐惧情绪的表达和调节[22]。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观察到的现象保持一致。
研究结果还观察到恐惧情绪能够激活边缘叶脑区,证实了边缘叶在情绪认知调节中的作用。之前临床研究证实了边缘叶病变的患者存在主观恐惧的认知调节和潜在的自主反应受损[23]。负性情绪可引起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活动变化。边缘叶位于大脑半球内侧面,边缘叶与杏仁核、前额叶等脑区之间存在一个管理情绪活动的工作网络,探索这个工作网络如何调节情绪活动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21]。
通过对250 ~ 450 ms脑电数据在溯源后做功能连接分析,在alpha频段发现不同情绪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观察到中性情绪的脑功能网络中连接边数量最少,且主要集中在额叶和一部分顶叶。而相比中性情绪,恐惧情绪的连接边数量明显更多,主要集中在颞叶和顶叶,表明负性情绪处理进程对大脑功能连接有着显著的影响。上述脑网络连接的结果或可揭示,在面对环境要求针对多样化的情绪刺激进行注意力分配的情境下,大脑内部alpha频段的功能连接模式会经历适应性重塑,以有效支持这一复杂的认知处理过程[24]。本研究截取EPN成分出现的EEG信号构建源层面脑网络,实现了以更高的时间分辨率分析情绪处理进程中的脑功能调制。
最后,通过计算脑网络属性,本研究发现与中性情绪相比,恐惧情绪的平均节点度和平均聚类系数明显更大。该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本研究中负性情绪视觉图片的刺激引发了受试者注意力的增加,反映在alpha大脑网络则表现为局部脑区信息处理能力的增强。之前的研究也已证实alpha频段可以用来研究对负性情绪刺激的注意力分配以及随后对外部环境的持续关注[25]。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探索人类大脑处理恐惧情绪刺激的神经机制提供了见解。研究观察到EPN振幅、皮层激活区域和脑网络连通性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的情绪信息是如何在人脑中被处理的,并为探索负面情绪的神经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臧倩负责实验设计、数据分析及论文写作;赵小茗负责数据收集和技术支持;梁铁、刘秀玲负责论文指导与修改;娄存广负责论文构思及论文校稿。
伦理声明:本研究通过了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批文编号:HDFYLL-KY-2024-009)。
0 引言
情绪是一种主观的体验,通常表现为对某种刺激的情感反应,如高兴、悲伤、厌恶、恐惧等。情绪对我们的思维、行为和身体反应产生影响,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恐惧作为常见的负性情绪,尽管已在生物学意义、生理基础及认知功能等多个维度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广泛研究,但恐惧情绪加工的神经机制仍不明确[1-3]。深入了解恐惧情绪背后的神经机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情感体验的产生和调节过程,进而进一步诊断和治疗与负性情绪相关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等。
之前基于脑成像的相关研究表明,恐惧刺激能够激活左舌回、左侧杏仁核以及左侧前额叶皮层等区域[4-5]。另外一些研究发现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对主观恐惧的认知调节起关键作用[6-7]。这些研究为证实恐惧情绪与特定脑区的激活存在相关性提供了充分证据。然而情绪的产生是瞬时发生的事件,脑成像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在时间分辨率上的不足限制了在更精细的时间过程中探索情绪处理机制。
得益于非侵入式神经电生理采集技术的发展,高时间分辨率的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信号被广泛应用于开展情绪研究。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技术能够反映特定事件刺激引起的大脑活动进程,是目前基于EEG信号开展情绪研究的重要方法[8-9]。早期后部负波(early posterior negativity,EPN)是当前ERP情绪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成分,它通常出现于视觉刺激呈现后的100 ~ 350 ms内,且在头皮颞枕部区域最为明显[10]。EPN反映了大脑对于视觉刺激的早期处理,被认为是与注意力资源量相关的选择性情绪感知的最早处理的标志[11]。先前的研究已证实EPN成分普遍存在于恐惧情绪刺激的实验条件下,并证实了EPN可以被用于表征大脑对恐惧情绪的视觉刺激信息的处理进程[12-13]。然而情绪产生是一种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大脑多区域的激活与相互作用[14]。尽管当前基于EPN的研究揭示了恐惧情绪处理过程中时间锁定的同步神经活动,但大多数忽略了大脑各区域在此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近年,网络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研究者们可以从网络的角度去研究情绪相关的大脑活动[15]。利用EEG信号构建并深入研究对应的脑功能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深入理解情绪处理过程中大脑全局调控机制的新视角,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情绪处理的神经机制。然而,大部分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大脑视觉刺激的信息处理进程,导致无法准确构建情绪处理过程中时间锁定的脑功能网络。而且,大部分基于EEG的脑功能网络的情绪研究都是利用头皮EEG信号来构建,而EEG信号存在严重的体积传导效应,这直接导致了它较低的空间分辨率,进而易导致脑功能网络构建不准确[16]。EEG溯源技术已被证实可以在确保EEG信号高时间分辨率的基础上有效提升其空间分辨率,有助于构建更准确的脑网络[17]。
本研究通过不同场景的情绪图片诱发健康受试者的恐惧和中性情绪,同步记录64通道EEG信号。随后,采用ERP技术探索两种情绪EPN成分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sLORETA方法对EEG信号执行溯源分析,进而基于图论构建并分析不同情绪状态下的源层面脑功能网络。本研究将ERP、EEG溯源以及脑网络分析相结合,探索视觉刺激诱发的恐惧情绪和中性情绪时间锁定的脑皮层电活动以及相关的脑网络调节机制,以期为负性情绪机制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为情绪障碍患者的诊疗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临床实践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本研究成功招募了20名健康成年受试者,包括10名男性和10名女性,年龄为(22.7 ± 2.2)岁。所有受试者均为右利手,且未患有任何精神类疾病。此外,所有受试者的视力或矫正视力均符合实验要求。在正式实验开始前,所有受试者详细了解了实验流程和需注意的事项,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由于实验中存在恐惧刺激,提前告知受试者能否接受,并且剔除掉胆子非常小和经常看恐怖电影的受试者,防止出现极端的个体差异。
所选刺激材料均为图片,选自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18]。首先在负性图片中初步选取了一些可能诱发恐惧的图片,代表图片有鬼脸、蛇、尸体和血腥等场景。考虑到每个人对恐惧的感受不同,负性图片再由受试者通过九点评分量表进行筛选,选取出他们认为恐惧和中性的图片。最终确定了30张恐惧图片(效价为2.38 ± 0.46,唤醒度为5.78 ± 0.63)。为防止恐惧图片连续多次出现引起的信息加工异化,又选取了60张中性图片(效价为5.49 ± 0.37,唤醒度为3.74 ± 0.51)。对所选材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恐惧图片的唤醒度和效价明显高于中性图片(P < 0.001)。
采用E-Prime 2.0专业软件编制实验范式,图片呈现于电脑屏幕。所有图片随机出现,均只出现一次。每试次开始时,黑色屏幕中央出现红色注视点,持续1 000 ms,之后呈现图片。每张图片的展示时间为3 000 ms,期间要求受试者保持自然注视状态,以便充分体验图片所诱发的情感反应。图片消失后,受试者需进行按键操作用于判断图片类型,其中1代表恐惧,2代表其他类别。整个实验流程如图1所示。实验总计120个试次,每30个试次受试者被允许休息一次。为让受试者熟悉实验流程,在正式实验开始前进行一次简单的预实验。在预实验中,选用同样来自IAPS的刺激图片,其中包括中性图片和恐惧图片各10张。预实验的操作流程严格遵循正式实验的标准,确保实验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实验在安静、光线暗的屏蔽室内进行,确保受试者身心放松并避免过多动作。
 图1
实验范式
图1
实验范式
实验开始时,屏幕中央出现红色注视点,持续1 000 ms。之后随机呈现情绪刺激图片3 000 ms。受试者在图片消失后通过按键判断图片类型(1为恐惧,2为其他)。右侧图片为恐惧情绪图片示例
Figure1. Experimental paradigmat the start of the experiment, a red fixation point appeared at the center of the screen and lasted for 1 000 ms. Subsequently, emotional stimulus images were randomly presented for 3 000 ms.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judge the type of the image (1 for fear, 2 for other) by pressing a key after the image disappeared. The four pictures on the right are examples of fear pictures
1.2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本研究中采用脑电采集系统(Neuroscan,澳大利亚)按照国际10-20标准以500 Hz采样率采集64通道EEG信号。实验过程中确保电极阻抗小于5 kΩ。EEG数据离线预处理在EEGLAB执行。首先将采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带通滤波(0.1~ 40 Hz),并根据信号质量决定是否剔除坏道,使用独立成分分析方法去除常见伪迹(如眼电、心电和肌电)。随后将幅值超过±100 μV的数据段全部剔除,有效数据长度设定为–200 ~ 3 000 ms(刺激图片出现时刻标注为0 ms,–200 ms代表刺激图片出现前200 ms)。同时去除受试者判断错误的试次,预处理后保留80%的有效试次,确保每个受试者每种条件下可供ERP分析的试次不少于23次。最终获得62导的EEG信号用于后续分析。在进行ERP分析时选取双侧乳突M1、M2为参考,在进行脑功能分析时参考改为全脑平均参考。
1.3 数据分析
首先,–200 ~ 800 ms的EEG数据被截取用于执行ERP分析。以刺激图片出现为0 ms,基线为图片呈现前200 ms,执行基线校正后分别对两种不同情绪刺激下的ERP活动进行叠加平均并进行统计分析。
随后,对包含EPN(250 ~ 450 ms)成分的EEG信号的平均波幅进行溯源分析。采用sLORETA算法,通过对采集到的头皮电极信号执行逆运算,求得大脑皮层各个脑区的电流密度分布[19]。在假定大脑皮层激活模式一致的前提下,分布于大脑皮层的电流密度源信号通过线性叠加的方式,最终在头皮上得以记录(即EEG信号)。
本研究使用Brainstorm软件实现溯源分析,采用t检验方法来检验条件之间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为进一步确定不同情绪下EPN成分的脑区连通性,将溯源后的EEG数据执行功能连接分析。采用相干性方法计算任意两脑区间的耦合强度作为节点连接边。
相干性作为衡量信号在特定频率下线性耦合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刻画了不同信号间的关联程度。给定信号x和y,它们之间的相干性可以通过式(1)进行量化描述为:
 |
式中,Pxy(f)代表信号x和y之间的交叉功率谱密度,而Pxx(f)和Pyy(f)代表各自的功率谱密度。
将之前sLORETA源定位的结果依据Desikan–Killiany–Tourville(DKT)模版映射至68个脑区,每个脑区的平均源信号作为该脑区的代表信号。分别在theta(4 ~ 8 Hz)、alpha(8 ~ 13 Hz)、beta(13 ~ 30 Hz)以及gamma(30 ~ 35 Hz)四个频段内计算平均源信号之间的相干性。最终每个受试者得到每种情绪下68*68*4的相干性矩阵。
分别在不同频段内对所有受试者两种情绪状态的连接矩阵检验零假设,即该条边的强度在不同情绪之间没有变化,采用的t统计量为:
 |
式中, 和
和 分别是两种情绪矩阵连接边的均值,
分别是两种情绪矩阵连接边的均值, 和
和 分别是两种情绪矩阵连接边的方差。通过置换检验(N = 10 000)来估计t统计量的分布,然后与原始值进行比较来确定每条边是否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选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连接矩阵所在频段。
分别是两种情绪矩阵连接边的方差。通过置换检验(N = 10 000)来估计t统计量的分布,然后与原始值进行比较来确定每条边是否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选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连接矩阵所在频段。
鉴于全连接矩阵在网络属性计算时涉及庞大的计算量,有必要对全连接矩阵进行阈值化处理。在阈值的选择上,研究者们常常以Kcost作为参考量来设定阈值,具体方式如式(3)所示:
 |
式中,Ki表示节点度,而N代表网络中节点总数。当Kcost的值等于P,并且处于0.05 ~ 0.35之间时,网络所展现出的拓扑结构属性与大脑网络的特性相近。此外,为了维持脑网络的连通性,网络的平均节点度应当满足一定的条件,即ln(N)≤Knet≤N。这一范围确保了脑网络在结构上的连通性与稳定性。本研究中,BrainNet Viewer软件被用于对阈值化后的连接矩阵进行可视化。
利用每个特定频段的脑网络计算网络属性,具体包括节点度和节点聚类系数。节点度表示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个数,即:
 |
式中,N表示网络中节点的总数,hij则代表矩阵中的相邻元素。
节点聚类系数是用来衡量一个节点与其邻近节点之间形成连接关系的可能性,反映了该节点在网络中的局部连接特性,即
 |
式中,Wi为与节点i相连的ki个节点间的实际连接边数,Mi为ki个节点间可能存在的最大连接边数,Ei表示节点i的ki个邻节点之间实际存在的边数。平均聚类系数则是对所有节点的聚类系数求平均值,提供了对整个网络局部连接紧密程度的整体评估。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两种情绪状态下的脑网络平均节点度和平均聚类系数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检验水准为0.05)。
2 结果
对于EPN成分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与中性情绪相比,恐惧情绪诱发了更大的EPN波幅(P < 0.05)。两种情绪条件下的ERP总平均波形见图2。
 图2
不同情绪图片刺激下代表性电极位置EPN总平均波形图
图2
不同情绪图片刺激下代表性电极位置EPN总平均波形图
图中阴影标注区域为出现的EPN成分
Figure2. Grand average waveform of the representative electrode position of EPN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pictures stimulithe shaded area in the figure indicates the occurrence of EPN components
由图3可见,恐惧情绪图片刺激下EPN成分的激活区域主要在缘上回、顶叶下回、左侧额中回下部、左侧颞下回、右侧颞叶、距状旁回、右侧楔前叶、扣带回峡部、前扣带回后部和右侧舌回,并且右侧顶叶下回的电流密度高于左侧。中性情绪图片刺激下EPN成分的激活区域主要为右枕叶外侧、右侧顶叶下回、左侧额中回下部、右侧额下回、右侧距状旁回、颞极区、额上回和内侧眶额。相比于恐惧情绪,中性情绪图片刺激下左脑的激活区域明显变少。
 图3
不同情绪图片刺激下的溯源分析结果及对比
Figure3.
Source analysis results and comparisons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pictures stimuli
图3
不同情绪图片刺激下的溯源分析结果及对比
Figure3.
Source analysis results and comparisons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pictures stimuli
进而,分析了两种情绪下大脑皮层活动差异的脑区,结果如图3所示。恐惧情绪和中性情绪的EPN源差异主要在右外侧眶额、左侧额中回下部、右侧额下回、右侧顶叶、左侧缘上回、左侧颞下回、右侧颞上回、右侧颞中回和楔前叶。
本研究针对每个受试者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四个频带脑网络进行了置换检验,仅在alpha频段发现了恐惧情绪与中性情绪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alpha频段下各情绪状态阈值化后的脑皮层功能网络(选取的阈值为0.5)如图4所示,可以看到,中性情绪状态下脑网络中连接边数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额叶和一部分顶叶。相比之下,恐惧情绪状态下连接数量明显更多,主要集中在颞叶和顶叶,表明负性情绪对大脑功能连接有着显著的影响。
 图4
不同情绪状态下alpha频段阈值化连接矩阵及脑网络
Figure4.
Thresholding connectivity matrix and visual brain network of alpha band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states
图4
不同情绪状态下alpha频段阈值化连接矩阵及脑网络
Figure4.
Thresholding connectivity matrix and visual brain network of alpha band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states
表1展示了恐惧情绪和中性情绪下脑网络的平均节点度和平均聚类系数。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与中性情绪相比,恐惧情绪状态下的脑网络表现出更高的平均节点度和平均聚类系数,这一发现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情绪状态对脑网络结构的影响。
3 讨论及结论
本研究将ERP、EEG溯源分析和源层面脑功能网络相结合,探索了视觉刺激诱发的恐惧和中性情绪的脑皮层活动及大脑功能调制。
本研究首先探索了恐惧和中性情绪刺激下EPN成分的差异。结果发现,相较于中性情绪,恐惧情绪诱发出了更高的EPN幅值。EPN作为一种ERP的重要成分,振幅被证实与情绪唤醒度相关,也与图片的情绪内容相关[20]。本研究中与刺激强度相关的EPN幅值增大的结果可能反映了情绪加工过程中注意力资源的分配,即相较于中性刺激,恐惧刺激更能引起受试者的注意[12]。本研究中,利用恐惧图片刺激受试者,观察到更为显著的EPN,这表明恐惧刺激有效激活了情绪生成系统,引发了受试者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应。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不同情绪状态会导致不同的大脑激活模式的观点。
通过对包含EPN成分的250 ~ 450 ms平均波幅的溯源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恐惧情绪和中性情绪EPN的源差异主要出现在右外侧眶额、左侧额中回下部、右侧额下回、右侧顶叶、左侧缘上回、左侧颞下回、右侧颞上回、右侧颞中回和楔前叶等区域。之前有研究认为左侧缘上回和左侧杏仁核在恐惧情绪的产生和表达中起重要作用,在面对威胁性刺激时,缘上回和杏仁核的活动会增加,并且与恐惧体验的强度呈正相关[21]。还有研究发现,左侧前额叶皮层和扣带回皮层也参与了恐惧情绪的表达和调节[22]。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观察到的现象保持一致。
研究结果还观察到恐惧情绪能够激活边缘叶脑区,证实了边缘叶在情绪认知调节中的作用。之前临床研究证实了边缘叶病变的患者存在主观恐惧的认知调节和潜在的自主反应受损[23]。负性情绪可引起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活动变化。边缘叶位于大脑半球内侧面,边缘叶与杏仁核、前额叶等脑区之间存在一个管理情绪活动的工作网络,探索这个工作网络如何调节情绪活动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21]。
通过对250 ~ 450 ms脑电数据在溯源后做功能连接分析,在alpha频段发现不同情绪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观察到中性情绪的脑功能网络中连接边数量最少,且主要集中在额叶和一部分顶叶。而相比中性情绪,恐惧情绪的连接边数量明显更多,主要集中在颞叶和顶叶,表明负性情绪处理进程对大脑功能连接有着显著的影响。上述脑网络连接的结果或可揭示,在面对环境要求针对多样化的情绪刺激进行注意力分配的情境下,大脑内部alpha频段的功能连接模式会经历适应性重塑,以有效支持这一复杂的认知处理过程[24]。本研究截取EPN成分出现的EEG信号构建源层面脑网络,实现了以更高的时间分辨率分析情绪处理进程中的脑功能调制。
最后,通过计算脑网络属性,本研究发现与中性情绪相比,恐惧情绪的平均节点度和平均聚类系数明显更大。该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本研究中负性情绪视觉图片的刺激引发了受试者注意力的增加,反映在alpha大脑网络则表现为局部脑区信息处理能力的增强。之前的研究也已证实alpha频段可以用来研究对负性情绪刺激的注意力分配以及随后对外部环境的持续关注[25]。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探索人类大脑处理恐惧情绪刺激的神经机制提供了见解。研究观察到EPN振幅、皮层激活区域和脑网络连通性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的情绪信息是如何在人脑中被处理的,并为探索负面情绪的神经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臧倩负责实验设计、数据分析及论文写作;赵小茗负责数据收集和技术支持;梁铁、刘秀玲负责论文指导与修改;娄存广负责论文构思及论文校稿。
伦理声明:本研究通过了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批文编号:HDFYLL-KY-2024-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