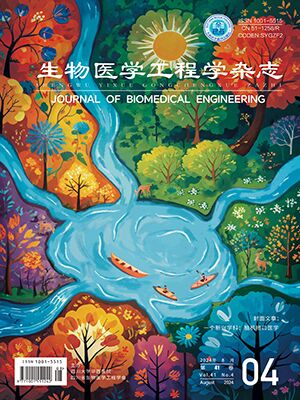缺血性卒中常会引起认知功能障碍,从而延缓了患者的康复进程,然而,其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本文以脑缺血再灌注模型为实验对象,以海马齿状回(DG)为目标脑区,TTC染色评估脑梗死程度,采集神经元膜电位和局部场电位(LFPs)信号,旨在探究脑缺血再灌注小鼠认知功能的损伤机制。结果发现,模型组小鼠大脑右侧梗死区呈白色;该模型小鼠海马DG神经元静息膜电位、动作电位放电个数、后超极化电位和最大上升斜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1),动作电位达峰时间、半波宽、阈值和最大下降斜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1)。缺血和缺血再灌注组小鼠在θ和γ频段的LFPs信号时频能量值显著降低(P < 0.01),但缺血再灌注组比缺血组明显提高(P < 0.01);缺血及缺血再灌注组的LFPs信号复杂度显著降低(P < 0.05),但缺血再灌注组与缺血组相比信号复杂度明显增加(P < 0.05)。综上所述,脑缺血再灌注使小鼠海马DG区神经元兴奋性降低;脑缺血使神经元放电活动和信号复杂度降低,经再灌注后电生理指标有所恢复,但实验周期内没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引用本文: 朱俞灿, 于洪丽, 赵秀芝, 王春方. 脑缺血再灌注小鼠海马齿状回神经兴奋性分析.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24, 41(5): 926-934. doi: 10.7507/1001-5515.202311055 复制
0 引言
缺血性脑卒中由区域脑血流量的短暂或永久性减少引起。据最新统计,每年有超过760万例新发缺血性卒中[1]。缺血性卒中除了可能导致肢体活动和语言能力等神经功能缺损以外,认知和记忆障碍是卒中后常见的后遗症之一[2]。有研究表明,认知损害与缺血性卒中患者的梗死程度以及病灶位置[3]、脑血管病变[4]、神经炎症[5]和血脑屏障破坏[6]等因素相关。海马是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脑区[7],其中,齿状回(dentate gyrus,DG)颗粒细胞在认知及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8]。然而,缺血性卒中对海马DG区神经活动的影响机制尚未明确。
电生理学方法一直是人们研究大脑神经活动的重要手段。先前的研究表明神经兴奋性的变化可能与认知缺陷相关[9-10],而神经元中安静时的静息膜电位、受到刺激时产生的动作电位的发放频率及其相关电特性指标是衡量神经元兴奋性的重要指标。局部场电位(local field potentials,LFPs)能够反映大脑局部神经元集群突触活动所造成的电场变化[11]。其中,θ频段(4~12 Hz)与学习和记忆有关[12],γ频段(30~100 Hz)在工作记忆的提取、形成等认知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13]。LFPs记录已被用于识别神经疾病的病理变化,检测进行性神经障碍的损伤程度。然而,以往关于缺血性卒中认知损伤的动物研究大多以行为学实验或者细胞生物学来展开探索[14-15],从电生理学角度研究卒中引起的海马神经活动变化的潜在机制较少。
缺血性卒中最常见于大脑中动脉及其分支阻塞[16]。再灌注现象指缺血性卒中在一段时间的缺血后重新获得血液供应的过程,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是缺血性卒中的普遍特征。故本文以大脑中动脉阻塞再灌注小鼠为实验对象,海马DG区为目标脑区,采用2, 3, 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2, 3, 5-triphenyltetrazolium chloride,TTC)评估该模型脑梗死程度,通过离体膜片钳和在体大脑LFPs探究脑缺血再灌注对小鼠海马DG神经元电生理特性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
本研究采用健康雄性C57BL/6小鼠,6~8周龄,体重(23 ± 3)g,共计26只。购自北京华阜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动物许可证号:SCXK(京)2019 - 0008。饲养环境温度维持在26 ℃左右,术前过夜禁食不禁水。所有实验均获得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本文总体研究路线图如图1所示。
 图1
总体研究路线图
Figure1.
Overall research roadmap
图1
总体研究路线图
Figure1.
Overall research roadmap
1.2 模型制备
采用线栓法[17]制备大脑中动脉阻塞再灌注小鼠模型。采用异氟烷搭配通氧的麻醉机对小鼠进行气麻,进入深度麻醉后,分离小鼠左侧颈总、颈外和颈内动脉,在颈总动脉上扎一小口,将线栓沿着颈内动脉插入,直至遇到轻微阻力不能再前送为止。整个手术过程为15~20 min,缺血60 min后拔除线栓实现再灌注。待小鼠有自主活动、刺激反应、正常姿势以及自主进食饮水等表现则表示小鼠完全清醒,后采用Zea-Longa神经功能评分对实验小鼠的神经功能缺陷程度进行评估,评分标准如表1所示。
采用TTC染色对脑组织损伤程度进行神经病理学评估,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模型组,每组4只。术后24 h,采用异氟烷待小鼠深度麻醉,断头取脑,切为连续冠状切片,放入2% TTC溶液中染色,后冲洗、固定脑片;染色结束后,选择适当的光源和角度,使用相机对脑片进行拍照以观察梗死面积。脑片中白色部分为梗死区域,红色部分为正常组织区域。
1.3 离体脑片膜片钳实验
1.3.1 试剂
① 人工脑脊液成分(单位均为mmol/L):NaCl 124、NaH2PO4 1.625、NaHCO3 26、葡萄糖 11、HEPES 5、KCl 3、CaCl2 2、MgCl2 2。② 高糖切片液成分(单位均为mmol/L):NaH2PO4 1.625、NaHCO3 26、葡萄糖 11、蔗糖 220、KCl 2.5、CaCl2 1、MgCl2 6。③ 膜片钳玻璃微电极内液成分(单位均为mmol/L):葡萄糖酸钾 140、MgCl2 1、HEPES 10、EGTA 0.2、Mg-ATP 4、Na2-GTP 0.3、磷酸肌酸钠 10。
1.3.2 脑片的制备与孵育
由于离体实验无法实时记录缺血期的膜电位信号,故本实验将小鼠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缺血再灌注组,每组6只。异氟烷麻醉小鼠后断头取脑,浸入氧饱和的冰水混合切片液;取出后大脑大口朝下粘于切片槽;使用振动切片机(VT1200S,Leica,德国)将大脑切成300 μm厚的切片;将有完整海马的脑片置于氧饱和的人工脑脊液中,后者盛于由亚克力板制成的容器盒内,于水浴锅中恒温28 ℃孵育60 min。
1.3.3 全细胞膜片钳记录
DG颗粒细胞作为信号记录的目标神经元。微电极拉制仪(P-97,SUTTER,美国)拉制玻璃微电极,用加液器将解冻后的电极内液经过滤充灌进电极尖端1/3处。将孵育好的脑片移入膜片钳操作台记录槽上,电极入液后调节微操将电极尖端移至细胞标记位置;电极尖端与细胞膜高阻封接后破膜,采用膜片钳信号放大器(EPC-10,HEKA,德国)全细胞电流钳记录模式,记录颗粒细胞的静息膜电位和动作电位等信号。
1.4 植入式多通道实验
1.4.1 电极植入与信号采集
本实验随机选取6只小鼠为实验对象,小鼠电极植入手术完成后分别采集对照、脑缺血和脑缺血再灌注三组静息状态下的LFPs信号。对所有小鼠进行16通道微电极阵列(4 × 4,Plexon,美国)植入手术,参考小鼠脑立体定位图谱[18],确定电极植入的位置。本实验中的微电极丝采用镍铬合金材质,每根电极丝的有效长度为15 mm,电极丝之间的垂直距离为200 μm。以前囟点为参考原点,定位海马DG区(前囟后1.5~2.5 mm,右旁开0.7~1.7 mm,深度2.5~2.6 mm)。之后在颅骨的目标区域钻1 mm × 1 mm的矩形窗口。将微电极阵列使用电动微推进器缓慢向下推进至目标脑区,最后封装固定电极。待小鼠恢复数天后,制备模型以采集缺血和再灌注信号。手术完成后待小鼠完全清醒,在缺血50 min左右开始记录缺血信号。拔除线栓后待小鼠恢复30 min左右开始采集再灌注信号。应用在体多通道神经电生理信号采集系统(OmniPlex128,Plexon,美国)采集小鼠损伤侧海马DG区的LFPs信号,信号的采样频率是1 kHz。
1.4.2 数据处理与分析
长时间记录LFPs信号会引入一些噪声干扰,如工频干扰和基线漂移等。因此,需对原始信号做预处理,如陷波滤波器去除50 Hz工频干扰及coif5小波基的小波重构去除基线漂移。基线漂移通常是低频信号的结果。对于非平稳信号,小波变换通过其多尺度分析能力可在低频尺度有效捕捉和分离成分同时尽量保留信号的有用信息,以得到平稳的16通道LFPs信号。随后应用巴特沃斯滤波器对预处理之后的信号提取与认知相关的θ与γ频段,频段信号波形图如图2所示。
 图2
θ频段与γ频段信号提取
Figure2.
θ-band and γ-band signal extraction
图2
θ频段与γ频段信号提取
Figure2.
θ-band and γ-band signal extraction
短时傅里叶变换(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STFT)[19]能够在时间上对信号进行分段处理并应用傅里叶变换。因此,本实验采用STFT分析缺血再灌注对小鼠海马DG区θ和γ频段信号时频能量的影响。其中,窗函数为hamming窗,窗口长度和移动步长分别为1 s和0.2 s。多尺度样本熵[20]通过粗粒化过程来衡量信号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复杂性。它能更大程度地表征出脑神经电信号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和监测。因此,使用多尺度样本熵算法计算三组小鼠海马DG区θ和γ频段信号的熵值,以探究缺血再灌注对小鼠海马LFPs信号复杂度的影响。其中,重构维数m = 2,阈值大小r = 0.15,尺度因子τ = 20。
1.4.3 电极植入位置的组织学检验
为了验证电极是否到达指定位置,在完成信号采集后对小鼠断头取脑,进行电极植入位置的组织学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通过小鼠脑组织的切片及相应的脑图谱对比分析,发现电极准确植入于海马DG区,符合实验预期。
 图3
电极植入海马位置的组织切片验证
Figure3.
Tissue section validation of electrode implantation in hippocampal locations
图3
电极植入海马位置的组织切片验证
Figure3.
Tissue section validation of electrode implantation in hippocampal locations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事后分析采用Tukey-test检验方法进行组间比较。统计结果均表示为均数±标准误。检验水准为0.05。
2 结果
2.1 模型评估
本文采用神经功能评分和TTC染色两种方法来评估脑缺血再灌注小鼠造模是否成功。其中神经功能评分结果显示,线栓法建立模型的方法评分在2~6分左右。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有明显的神经功能缺损表现(P < 0.05),之后选取符合评分标准的小鼠纳入后续实验。脑缺血再灌注24 h后,模型组小鼠大脑右侧梗死区呈白色,如图4所示。模型组脑梗死面积占大脑总面积的(37.88 ± 12.30)%,与对照组(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以上结果说明本文使用线栓法诱导大脑中动脉阻塞再灌注模型造模成功。
 图4
TTC染色结果
Figure4.
TTC staining results
图4
TTC染色结果
Figure4.
TTC staining results
2.2 缺血再灌注对海马DG颗粒细胞神经兴奋性的影响
在全细胞电流钳模式中,对照组和缺血再灌注组各选取18个颗粒细胞,记录并分析两组神经元细胞的神经兴奋性相关电特性指标。诱发刺激程序设置为初始值0 pA、固定步长10 pA、时长为500 ms的去极化电流诱发神经放电。其中,膜电位相关指标示意图如图5所示。
 图5
神经元膜电位指标示意图
Figure5.
Diagram of nerve cell membrane potential index
图5
神经元膜电位指标示意图
Figure5.
Diagram of nerve cell membrane potential index
对两组小鼠神经元静息膜电位及动作电位相关指标的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缺血再灌注组的静息膜电位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1),两组小鼠之间的峰值电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缺血再灌注组的动作电位放电个数、后超极化电位和最大上升斜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1),缺血再灌注组的动作电位达峰时间、半波宽、阈值电位和最大下降斜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1)。
 图6
神经元静息膜电位及动作电位相关指标(**P < 0.01)
Figure6.
Relative indexes of 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 and action potential of nerve cells (**P < 0.01)
图6
神经元静息膜电位及动作电位相关指标(**P < 0.01)
Figure6.
Relative indexes of 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 and action potential of nerve cells (**P < 0.01)
2.3 缺血再灌注小鼠海马DG区局部场电位信号分析
2.3.1 时频分析结果
选取每只小鼠30次、每次4 000 ms的LFPs信号,分析其低频θ和高频γ频段时频特性。图7为对照组、缺血组和缺血再灌注组小鼠θ频段信号的时频能量分布图。由图可以看出,与对照组相比,缺血组和缺血再灌注组小鼠时频能量均降低,同时缺血再灌注组时频能量高于缺血组小鼠。图8为三组小鼠γ频段信号的时频能量分布图。由图可以看出,与对照组相比,缺血组和缺血再灌注组小鼠γ频段能量值整体较低;而与缺血组相比,缺血再灌注组小鼠能量有所增强。
 图7
θ频段LFPs时频能量分布
Figure7.
Time-frequency energy distribution of LFPs in θ band
图7
θ频段LFPs时频能量分布
Figure7.
Time-frequency energy distribution of LFPs in θ band
 图8
γ频段LFPs时频能量分布
Figure8.
Time-frequency energy distribution of LFPs in γ band
图8
γ频段LFPs时频能量分布
Figure8.
Time-frequency energy distribution of LFPs in γ band
将LFPs信号时频能量值进行平均,结果如图9所示。经统计分析发现,缺血组和缺血再灌注组θ频段信号的平均能量值均低于对照组且有明显差异(P < 0.01),而缺血再灌注组θ频段信号的平均能量值显著高于缺血组(P < 0.01);同样,缺血和缺血再灌注组γ频段信号的平均能量值均低于对照组(P < 0.01),但缺血再灌注组γ频段信号的平均能量值高于缺血组(P < 0.01)。
 图9
两频段平均能量对比(**P < 0.01)
Figure9.
Average energy comparison of two frequency bands (**P < 0.01)
图9
两频段平均能量对比(**P < 0.01)
Figure9.
Average energy comparison of two frequency bands (**P < 0.01)
2.3.2 信号复杂度分析结果
计算θ频段信号多尺度样本熵,结果如图10左图所示。可以看出,三组小鼠海马DG区θ频段信号熵值均随尺度的增大不断增加,且对照组熵值在所有尺度上均显著高于缺血组(P < 0.05),部分尺度上显著高于缺血再灌注组(P < 0.05);缺血组熵值在所有尺度上均低于缺血再灌注组(P < 0.05)。
 图10
LFPs信号两频段复杂度对比(*P < 0.05)
Figure10.
Complexity comparison of two bands of LFPs signals (*P < 0.05)
图10
LFPs信号两频段复杂度对比(*P < 0.05)
Figure10.
Complexity comparison of two bands of LFPs signals (*P < 0.05)
γ频段信号多尺度样本熵值如图10右图所示。可以看出,三组小鼠海马DG区γ频段信号熵值随尺度先增加后减小。对照组熵值在所有尺度上均显著高于缺血组和缺血再灌注组(P < 0.05);缺血组熵值在部分尺度上低于缺血再灌注组(P < 0.05)。
3 讨论
不同大脑区域的局部损伤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该现象在缺血性卒中后较为常见[21-22]。有研究指出海马DG区受损时,大部分海马依赖的认知功能也会降低[23]。然而,缺血性卒中是否会影响大脑海马DG区神经元电活动目前还尚未明确。本文通过静息膜电位及动作电位相关指标分析发现,脑缺血再灌注降低了小鼠海马DG区神经元的静息膜电位;在去极化电流刺激作用下,脑缺血再灌注小鼠的动作电位放电个数显著减少,诱发放电频率减弱,说明该模型鼠在静息状态下神经元兴奋性降低,细胞膜去极化产生神经放电所需的刺激更大;动作电位达峰时间与最大上升斜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达峰时间越长代表离子通道的开放与关闭的速度越慢,去极化的过程越缓慢,上升斜率越小;最大下降斜率越大说明复极化的过程越迅速;半波宽反映整个动作电位的时程,阈值电位是神经元受到刺激时刚好能触发动作电位膜电位的临界值,半波宽和阈值电位的增加意味着神经元将更难产生动作电位。后超极化电位的降低说明复极化后神经元静息膜电位处于更低水平,再次受到刺激时神经元将更难以兴奋。综合以上结果说明脑缺血再灌注有可能会导致小鼠海马DG区神经元电特性指标异常,神经元兴奋性降低。而神经元兴奋性是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的基础,神经元兴奋性的异常调节可能与相关神经性疾病认知障碍等症状的发展有关[24]。之前有研究发现海马中的神经元可能是通过调节DG区网络的兴奋性来促进认知过程的[25],缺血再灌注的改善可能与增强同侧半球神经元的兴奋性等因素有关[26]。由此我们认为,脑缺血再灌注过程可导致海马等认知功能相关脑区神经元兴奋性降低,这可能是缺血性卒中引发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之一。
对海马DG区LFPs信号分析结果显示,缺血组小鼠海马DG区LFPs信号θ和γ频段能量减弱,再灌注后信号能量有所增强。脑缺血还降低了小鼠海马DG区θ和γ频段的信号复杂度,经再灌注后信号复杂度有一定程度提升,但仍低于正常小鼠水平。分析原因可能是缺血时期大脑血流受阻,区域脑组织神经元电活动受到抑制,信号复杂度降低。而再灌注后血流得到回升,神经元电活动得以恢复,信号复杂度升高,但有限时间内仍无法达到正常水平。之前有学者指出缺血性卒中对海马区电生理学的影响表现为破坏锐波相关涟漪和海马体内以及皮层与海马间的相位振幅耦合,从而改变了大脑状态[27]。He等[28]研究发现脑缺血可能破坏海马体兴奋性和抑制性回路之间的平衡,大鼠大脑远端中动脉闭塞期间海马θ和γ振荡功率暂时降低和高θ持续时间缩短,只有缺血再灌注后才检测到对记忆巩固至关重要的尖锐波相关波纹增加。Sutherland等[29]监测脑缺血和再灌注过程中的大脑活动以及时间依赖性神经生理学和血流动力学反应,结果发现该模型的诱发血流量、组织氧合和神经元活动减弱,并在再灌注过程中部分恢复。Sato等[30]也提到脑梗死发生后由于能量供应缺乏使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发生去极化,而再灌注一段时间后该过程停止。综合以上分析来看,本文研究结果与前述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4 结论
本文通过离体和在体电生理方法探究了缺血再灌注小鼠海马DG区神经元电生理特性的变化。对静息膜电位、动作电位及其相关电特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缺血再灌注严重影响了小鼠海马DG区颗粒细胞神经元的活动变化,表现为神经元电特性指标异常,神经元兴奋性降低。LFPs信号分析结果表明,脑缺血后小鼠海马DG区θ和γ频段信号的神经放电活动减弱,信号复杂度降低,经再灌注后神经放电活动和信号复杂度有一定程度提升,但实验周期内没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本研究为进一步探究缺血性卒中引起海马神经活动变化的潜在机制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朱俞灿参与了实验设计、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论文写作;于洪丽参与了论文的选题、实验设计和论文内容审核;赵秀芝参与了实验设计和数据采集;王春方参与了实验设计和论文修改。
伦理声明:本研究通过了河北工业大学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批文编号:HEBUTaCUC2022066)。
0 引言
缺血性脑卒中由区域脑血流量的短暂或永久性减少引起。据最新统计,每年有超过760万例新发缺血性卒中[1]。缺血性卒中除了可能导致肢体活动和语言能力等神经功能缺损以外,认知和记忆障碍是卒中后常见的后遗症之一[2]。有研究表明,认知损害与缺血性卒中患者的梗死程度以及病灶位置[3]、脑血管病变[4]、神经炎症[5]和血脑屏障破坏[6]等因素相关。海马是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脑区[7],其中,齿状回(dentate gyrus,DG)颗粒细胞在认知及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8]。然而,缺血性卒中对海马DG区神经活动的影响机制尚未明确。
电生理学方法一直是人们研究大脑神经活动的重要手段。先前的研究表明神经兴奋性的变化可能与认知缺陷相关[9-10],而神经元中安静时的静息膜电位、受到刺激时产生的动作电位的发放频率及其相关电特性指标是衡量神经元兴奋性的重要指标。局部场电位(local field potentials,LFPs)能够反映大脑局部神经元集群突触活动所造成的电场变化[11]。其中,θ频段(4~12 Hz)与学习和记忆有关[12],γ频段(30~100 Hz)在工作记忆的提取、形成等认知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13]。LFPs记录已被用于识别神经疾病的病理变化,检测进行性神经障碍的损伤程度。然而,以往关于缺血性卒中认知损伤的动物研究大多以行为学实验或者细胞生物学来展开探索[14-15],从电生理学角度研究卒中引起的海马神经活动变化的潜在机制较少。
缺血性卒中最常见于大脑中动脉及其分支阻塞[16]。再灌注现象指缺血性卒中在一段时间的缺血后重新获得血液供应的过程,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是缺血性卒中的普遍特征。故本文以大脑中动脉阻塞再灌注小鼠为实验对象,海马DG区为目标脑区,采用2, 3, 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2, 3, 5-triphenyltetrazolium chloride,TTC)评估该模型脑梗死程度,通过离体膜片钳和在体大脑LFPs探究脑缺血再灌注对小鼠海马DG神经元电生理特性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
本研究采用健康雄性C57BL/6小鼠,6~8周龄,体重(23 ± 3)g,共计26只。购自北京华阜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动物许可证号:SCXK(京)2019 - 0008。饲养环境温度维持在26 ℃左右,术前过夜禁食不禁水。所有实验均获得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本文总体研究路线图如图1所示。
 图1
总体研究路线图
Figure1.
Overall research roadmap
图1
总体研究路线图
Figure1.
Overall research roadmap
1.2 模型制备
采用线栓法[17]制备大脑中动脉阻塞再灌注小鼠模型。采用异氟烷搭配通氧的麻醉机对小鼠进行气麻,进入深度麻醉后,分离小鼠左侧颈总、颈外和颈内动脉,在颈总动脉上扎一小口,将线栓沿着颈内动脉插入,直至遇到轻微阻力不能再前送为止。整个手术过程为15~20 min,缺血60 min后拔除线栓实现再灌注。待小鼠有自主活动、刺激反应、正常姿势以及自主进食饮水等表现则表示小鼠完全清醒,后采用Zea-Longa神经功能评分对实验小鼠的神经功能缺陷程度进行评估,评分标准如表1所示。
采用TTC染色对脑组织损伤程度进行神经病理学评估,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模型组,每组4只。术后24 h,采用异氟烷待小鼠深度麻醉,断头取脑,切为连续冠状切片,放入2% TTC溶液中染色,后冲洗、固定脑片;染色结束后,选择适当的光源和角度,使用相机对脑片进行拍照以观察梗死面积。脑片中白色部分为梗死区域,红色部分为正常组织区域。
1.3 离体脑片膜片钳实验
1.3.1 试剂
① 人工脑脊液成分(单位均为mmol/L):NaCl 124、NaH2PO4 1.625、NaHCO3 26、葡萄糖 11、HEPES 5、KCl 3、CaCl2 2、MgCl2 2。② 高糖切片液成分(单位均为mmol/L):NaH2PO4 1.625、NaHCO3 26、葡萄糖 11、蔗糖 220、KCl 2.5、CaCl2 1、MgCl2 6。③ 膜片钳玻璃微电极内液成分(单位均为mmol/L):葡萄糖酸钾 140、MgCl2 1、HEPES 10、EGTA 0.2、Mg-ATP 4、Na2-GTP 0.3、磷酸肌酸钠 10。
1.3.2 脑片的制备与孵育
由于离体实验无法实时记录缺血期的膜电位信号,故本实验将小鼠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缺血再灌注组,每组6只。异氟烷麻醉小鼠后断头取脑,浸入氧饱和的冰水混合切片液;取出后大脑大口朝下粘于切片槽;使用振动切片机(VT1200S,Leica,德国)将大脑切成300 μm厚的切片;将有完整海马的脑片置于氧饱和的人工脑脊液中,后者盛于由亚克力板制成的容器盒内,于水浴锅中恒温28 ℃孵育60 min。
1.3.3 全细胞膜片钳记录
DG颗粒细胞作为信号记录的目标神经元。微电极拉制仪(P-97,SUTTER,美国)拉制玻璃微电极,用加液器将解冻后的电极内液经过滤充灌进电极尖端1/3处。将孵育好的脑片移入膜片钳操作台记录槽上,电极入液后调节微操将电极尖端移至细胞标记位置;电极尖端与细胞膜高阻封接后破膜,采用膜片钳信号放大器(EPC-10,HEKA,德国)全细胞电流钳记录模式,记录颗粒细胞的静息膜电位和动作电位等信号。
1.4 植入式多通道实验
1.4.1 电极植入与信号采集
本实验随机选取6只小鼠为实验对象,小鼠电极植入手术完成后分别采集对照、脑缺血和脑缺血再灌注三组静息状态下的LFPs信号。对所有小鼠进行16通道微电极阵列(4 × 4,Plexon,美国)植入手术,参考小鼠脑立体定位图谱[18],确定电极植入的位置。本实验中的微电极丝采用镍铬合金材质,每根电极丝的有效长度为15 mm,电极丝之间的垂直距离为200 μm。以前囟点为参考原点,定位海马DG区(前囟后1.5~2.5 mm,右旁开0.7~1.7 mm,深度2.5~2.6 mm)。之后在颅骨的目标区域钻1 mm × 1 mm的矩形窗口。将微电极阵列使用电动微推进器缓慢向下推进至目标脑区,最后封装固定电极。待小鼠恢复数天后,制备模型以采集缺血和再灌注信号。手术完成后待小鼠完全清醒,在缺血50 min左右开始记录缺血信号。拔除线栓后待小鼠恢复30 min左右开始采集再灌注信号。应用在体多通道神经电生理信号采集系统(OmniPlex128,Plexon,美国)采集小鼠损伤侧海马DG区的LFPs信号,信号的采样频率是1 kHz。
1.4.2 数据处理与分析
长时间记录LFPs信号会引入一些噪声干扰,如工频干扰和基线漂移等。因此,需对原始信号做预处理,如陷波滤波器去除50 Hz工频干扰及coif5小波基的小波重构去除基线漂移。基线漂移通常是低频信号的结果。对于非平稳信号,小波变换通过其多尺度分析能力可在低频尺度有效捕捉和分离成分同时尽量保留信号的有用信息,以得到平稳的16通道LFPs信号。随后应用巴特沃斯滤波器对预处理之后的信号提取与认知相关的θ与γ频段,频段信号波形图如图2所示。
 图2
θ频段与γ频段信号提取
Figure2.
θ-band and γ-band signal extraction
图2
θ频段与γ频段信号提取
Figure2.
θ-band and γ-band signal extraction
短时傅里叶变换(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STFT)[19]能够在时间上对信号进行分段处理并应用傅里叶变换。因此,本实验采用STFT分析缺血再灌注对小鼠海马DG区θ和γ频段信号时频能量的影响。其中,窗函数为hamming窗,窗口长度和移动步长分别为1 s和0.2 s。多尺度样本熵[20]通过粗粒化过程来衡量信号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复杂性。它能更大程度地表征出脑神经电信号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和监测。因此,使用多尺度样本熵算法计算三组小鼠海马DG区θ和γ频段信号的熵值,以探究缺血再灌注对小鼠海马LFPs信号复杂度的影响。其中,重构维数m = 2,阈值大小r = 0.15,尺度因子τ = 20。
1.4.3 电极植入位置的组织学检验
为了验证电极是否到达指定位置,在完成信号采集后对小鼠断头取脑,进行电极植入位置的组织学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通过小鼠脑组织的切片及相应的脑图谱对比分析,发现电极准确植入于海马DG区,符合实验预期。
 图3
电极植入海马位置的组织切片验证
Figure3.
Tissue section validation of electrode implantation in hippocampal locations
图3
电极植入海马位置的组织切片验证
Figure3.
Tissue section validation of electrode implantation in hippocampal locations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事后分析采用Tukey-test检验方法进行组间比较。统计结果均表示为均数±标准误。检验水准为0.05。
2 结果
2.1 模型评估
本文采用神经功能评分和TTC染色两种方法来评估脑缺血再灌注小鼠造模是否成功。其中神经功能评分结果显示,线栓法建立模型的方法评分在2~6分左右。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有明显的神经功能缺损表现(P < 0.05),之后选取符合评分标准的小鼠纳入后续实验。脑缺血再灌注24 h后,模型组小鼠大脑右侧梗死区呈白色,如图4所示。模型组脑梗死面积占大脑总面积的(37.88 ± 12.30)%,与对照组(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以上结果说明本文使用线栓法诱导大脑中动脉阻塞再灌注模型造模成功。
 图4
TTC染色结果
Figure4.
TTC staining results
图4
TTC染色结果
Figure4.
TTC staining results
2.2 缺血再灌注对海马DG颗粒细胞神经兴奋性的影响
在全细胞电流钳模式中,对照组和缺血再灌注组各选取18个颗粒细胞,记录并分析两组神经元细胞的神经兴奋性相关电特性指标。诱发刺激程序设置为初始值0 pA、固定步长10 pA、时长为500 ms的去极化电流诱发神经放电。其中,膜电位相关指标示意图如图5所示。
 图5
神经元膜电位指标示意图
Figure5.
Diagram of nerve cell membrane potential index
图5
神经元膜电位指标示意图
Figure5.
Diagram of nerve cell membrane potential index
对两组小鼠神经元静息膜电位及动作电位相关指标的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缺血再灌注组的静息膜电位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1),两组小鼠之间的峰值电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缺血再灌注组的动作电位放电个数、后超极化电位和最大上升斜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1),缺血再灌注组的动作电位达峰时间、半波宽、阈值电位和最大下降斜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1)。
 图6
神经元静息膜电位及动作电位相关指标(**P < 0.01)
Figure6.
Relative indexes of 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 and action potential of nerve cells (**P < 0.01)
图6
神经元静息膜电位及动作电位相关指标(**P < 0.01)
Figure6.
Relative indexes of 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 and action potential of nerve cells (**P < 0.01)
2.3 缺血再灌注小鼠海马DG区局部场电位信号分析
2.3.1 时频分析结果
选取每只小鼠30次、每次4 000 ms的LFPs信号,分析其低频θ和高频γ频段时频特性。图7为对照组、缺血组和缺血再灌注组小鼠θ频段信号的时频能量分布图。由图可以看出,与对照组相比,缺血组和缺血再灌注组小鼠时频能量均降低,同时缺血再灌注组时频能量高于缺血组小鼠。图8为三组小鼠γ频段信号的时频能量分布图。由图可以看出,与对照组相比,缺血组和缺血再灌注组小鼠γ频段能量值整体较低;而与缺血组相比,缺血再灌注组小鼠能量有所增强。
 图7
θ频段LFPs时频能量分布
Figure7.
Time-frequency energy distribution of LFPs in θ band
图7
θ频段LFPs时频能量分布
Figure7.
Time-frequency energy distribution of LFPs in θ band
 图8
γ频段LFPs时频能量分布
Figure8.
Time-frequency energy distribution of LFPs in γ band
图8
γ频段LFPs时频能量分布
Figure8.
Time-frequency energy distribution of LFPs in γ band
将LFPs信号时频能量值进行平均,结果如图9所示。经统计分析发现,缺血组和缺血再灌注组θ频段信号的平均能量值均低于对照组且有明显差异(P < 0.01),而缺血再灌注组θ频段信号的平均能量值显著高于缺血组(P < 0.01);同样,缺血和缺血再灌注组γ频段信号的平均能量值均低于对照组(P < 0.01),但缺血再灌注组γ频段信号的平均能量值高于缺血组(P < 0.01)。
 图9
两频段平均能量对比(**P < 0.01)
Figure9.
Average energy comparison of two frequency bands (**P < 0.01)
图9
两频段平均能量对比(**P < 0.01)
Figure9.
Average energy comparison of two frequency bands (**P < 0.01)
2.3.2 信号复杂度分析结果
计算θ频段信号多尺度样本熵,结果如图10左图所示。可以看出,三组小鼠海马DG区θ频段信号熵值均随尺度的增大不断增加,且对照组熵值在所有尺度上均显著高于缺血组(P < 0.05),部分尺度上显著高于缺血再灌注组(P < 0.05);缺血组熵值在所有尺度上均低于缺血再灌注组(P < 0.05)。
 图10
LFPs信号两频段复杂度对比(*P < 0.05)
Figure10.
Complexity comparison of two bands of LFPs signals (*P < 0.05)
图10
LFPs信号两频段复杂度对比(*P < 0.05)
Figure10.
Complexity comparison of two bands of LFPs signals (*P < 0.05)
γ频段信号多尺度样本熵值如图10右图所示。可以看出,三组小鼠海马DG区γ频段信号熵值随尺度先增加后减小。对照组熵值在所有尺度上均显著高于缺血组和缺血再灌注组(P < 0.05);缺血组熵值在部分尺度上低于缺血再灌注组(P < 0.05)。
3 讨论
不同大脑区域的局部损伤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该现象在缺血性卒中后较为常见[21-22]。有研究指出海马DG区受损时,大部分海马依赖的认知功能也会降低[23]。然而,缺血性卒中是否会影响大脑海马DG区神经元电活动目前还尚未明确。本文通过静息膜电位及动作电位相关指标分析发现,脑缺血再灌注降低了小鼠海马DG区神经元的静息膜电位;在去极化电流刺激作用下,脑缺血再灌注小鼠的动作电位放电个数显著减少,诱发放电频率减弱,说明该模型鼠在静息状态下神经元兴奋性降低,细胞膜去极化产生神经放电所需的刺激更大;动作电位达峰时间与最大上升斜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达峰时间越长代表离子通道的开放与关闭的速度越慢,去极化的过程越缓慢,上升斜率越小;最大下降斜率越大说明复极化的过程越迅速;半波宽反映整个动作电位的时程,阈值电位是神经元受到刺激时刚好能触发动作电位膜电位的临界值,半波宽和阈值电位的增加意味着神经元将更难产生动作电位。后超极化电位的降低说明复极化后神经元静息膜电位处于更低水平,再次受到刺激时神经元将更难以兴奋。综合以上结果说明脑缺血再灌注有可能会导致小鼠海马DG区神经元电特性指标异常,神经元兴奋性降低。而神经元兴奋性是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的基础,神经元兴奋性的异常调节可能与相关神经性疾病认知障碍等症状的发展有关[24]。之前有研究发现海马中的神经元可能是通过调节DG区网络的兴奋性来促进认知过程的[25],缺血再灌注的改善可能与增强同侧半球神经元的兴奋性等因素有关[26]。由此我们认为,脑缺血再灌注过程可导致海马等认知功能相关脑区神经元兴奋性降低,这可能是缺血性卒中引发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之一。
对海马DG区LFPs信号分析结果显示,缺血组小鼠海马DG区LFPs信号θ和γ频段能量减弱,再灌注后信号能量有所增强。脑缺血还降低了小鼠海马DG区θ和γ频段的信号复杂度,经再灌注后信号复杂度有一定程度提升,但仍低于正常小鼠水平。分析原因可能是缺血时期大脑血流受阻,区域脑组织神经元电活动受到抑制,信号复杂度降低。而再灌注后血流得到回升,神经元电活动得以恢复,信号复杂度升高,但有限时间内仍无法达到正常水平。之前有学者指出缺血性卒中对海马区电生理学的影响表现为破坏锐波相关涟漪和海马体内以及皮层与海马间的相位振幅耦合,从而改变了大脑状态[27]。He等[28]研究发现脑缺血可能破坏海马体兴奋性和抑制性回路之间的平衡,大鼠大脑远端中动脉闭塞期间海马θ和γ振荡功率暂时降低和高θ持续时间缩短,只有缺血再灌注后才检测到对记忆巩固至关重要的尖锐波相关波纹增加。Sutherland等[29]监测脑缺血和再灌注过程中的大脑活动以及时间依赖性神经生理学和血流动力学反应,结果发现该模型的诱发血流量、组织氧合和神经元活动减弱,并在再灌注过程中部分恢复。Sato等[30]也提到脑梗死发生后由于能量供应缺乏使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发生去极化,而再灌注一段时间后该过程停止。综合以上分析来看,本文研究结果与前述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4 结论
本文通过离体和在体电生理方法探究了缺血再灌注小鼠海马DG区神经元电生理特性的变化。对静息膜电位、动作电位及其相关电特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缺血再灌注严重影响了小鼠海马DG区颗粒细胞神经元的活动变化,表现为神经元电特性指标异常,神经元兴奋性降低。LFPs信号分析结果表明,脑缺血后小鼠海马DG区θ和γ频段信号的神经放电活动减弱,信号复杂度降低,经再灌注后神经放电活动和信号复杂度有一定程度提升,但实验周期内没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本研究为进一步探究缺血性卒中引起海马神经活动变化的潜在机制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朱俞灿参与了实验设计、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论文写作;于洪丽参与了论文的选题、实验设计和论文内容审核;赵秀芝参与了实验设计和数据采集;王春方参与了实验设计和论文修改。
伦理声明:本研究通过了河北工业大学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批文编号:HEBUTaCUC2022066)。